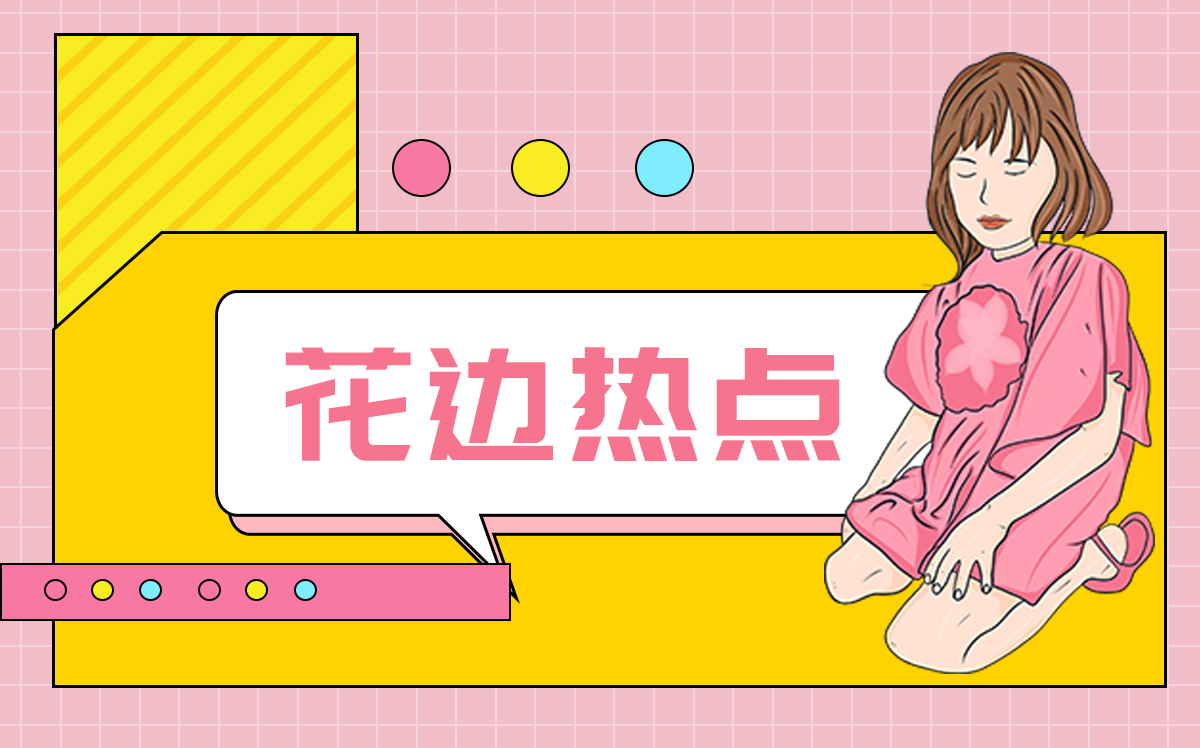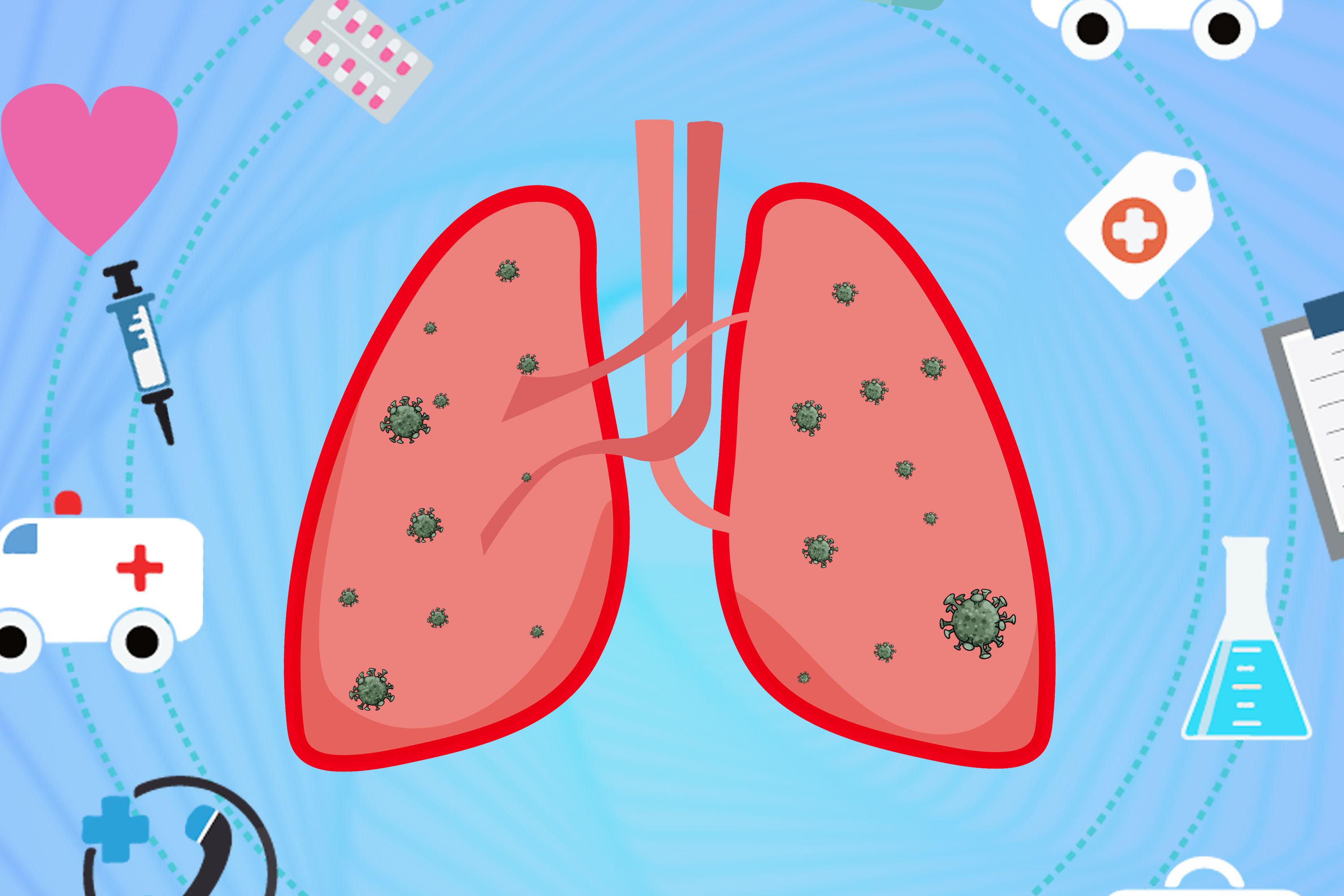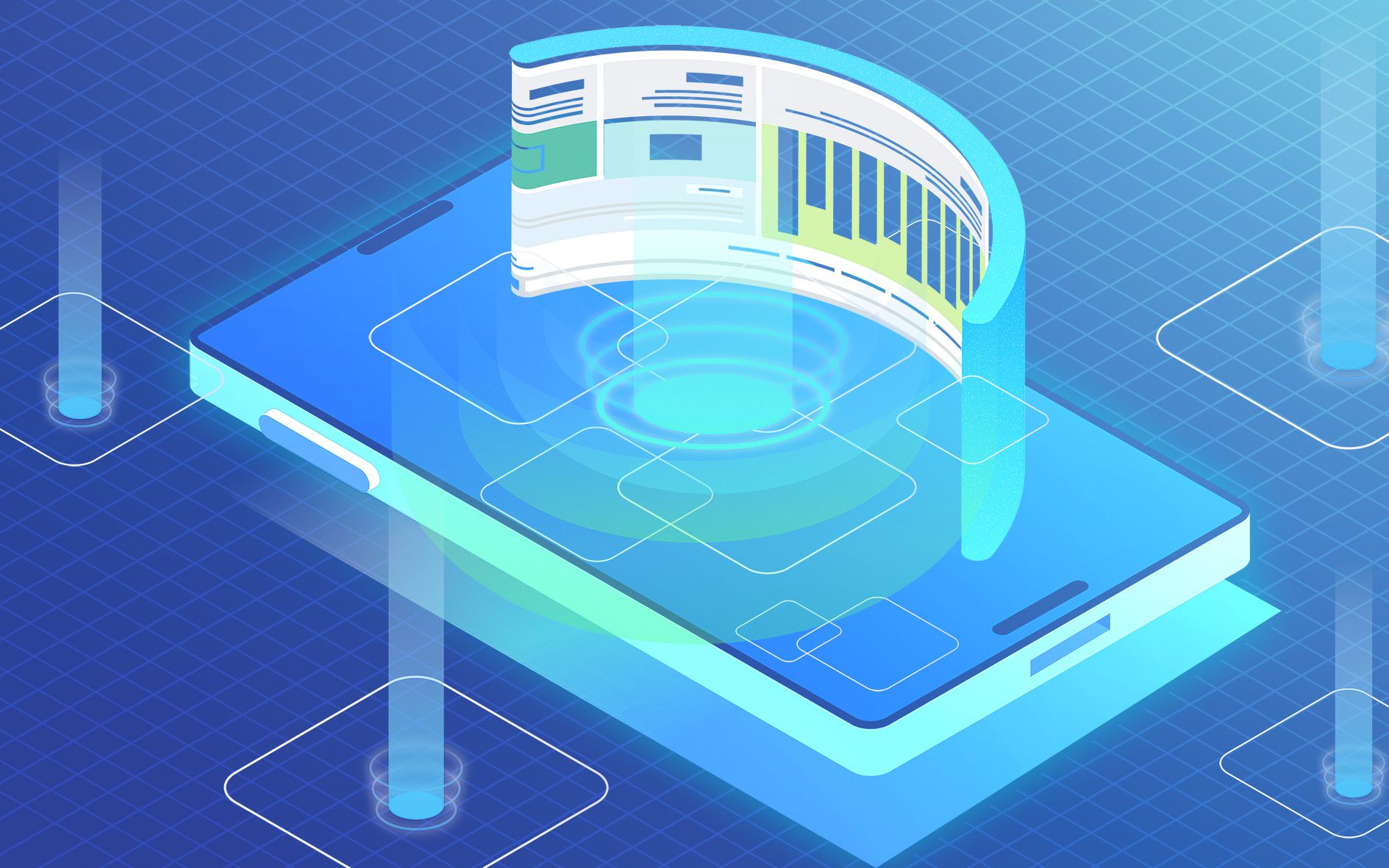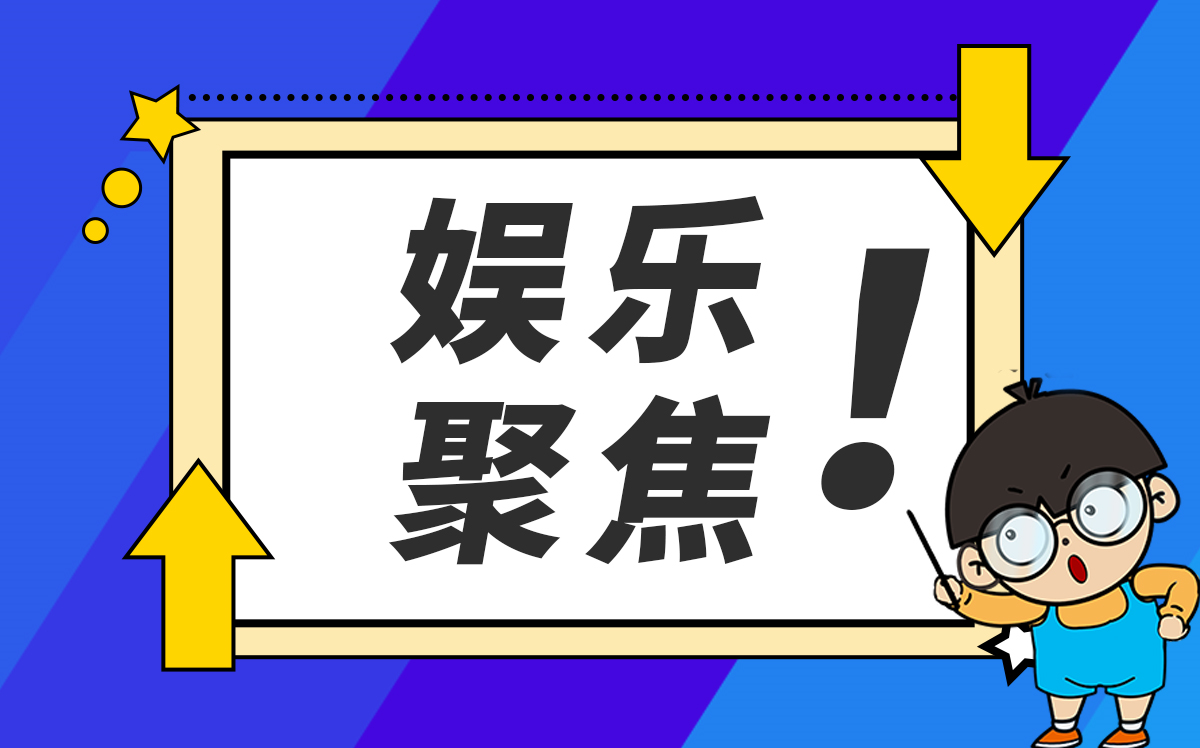坐落在广西上林县清水河畔崇山峻岭之中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简称《大宅颂》)与《廖州刺史韦敬辨智城碑》(简称《智城碑》),分别刻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和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距今有1300多年,是岭南地区年代最早的两块唐碑。由于《大宅颂》《智城碑》均为山峦岩壁间的摩崖石刻,而且地处偏隅深邃、交通不畅之地,故两块碑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藏存深山、少为人知。最早记载《智城碑》的典籍为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智城洞,去县四十里,盖韦厥所隐之洞也。碑乃廖州刺史韦敬辨所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认为,在《舆地纪胜》地理书中讲到智城洞、智城碑,这个地点一直以来,在大众印象中不太清楚,所以到明清时期好多搞古代碑刻的人来寻找,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有的以为在象州,有的甚至以为在龙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 蒋廷瑜)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由宋至清,金石类书籍中有提及《智城碑》,多为辗转抄录,著书者并未见过该唐碑实物或拓片。直到清道光年间,思恩府知府李彦章深入上林,将《智城碑》拓下,填补了“《智城碑》向无拓本”的历史空白,也让《智城碑》声闻天下。
受其影响,晚清至民国时期,金石家争相前来捶拓原碑。《大宅颂》与《智城碑》相距不过10里,也因此在世间留下拓本。其后因国内战乱频发,《大宅颂》与《智城碑》又沉寂在深山之中。新中国建立后,广西考古界派出考古专家寻访两块唐碑,最终在上林的澄泰乡和白圩镇一带找到了它们的位置。1963年,《大宅颂》与《智城碑》被公布为自治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舆地纪胜》中所提到的智城洞,即产生《智城碑》的母体——智城,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构的,在广西考古学界一直是个谜团。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上林县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在《智城碑》附近发现了多处古城墙遗址和文化遗存,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介绍,这个城址与碑像描述的是一致的,周围都是石山,只是从东南部有个入口。且在里面发掘有水井,有石碾、有石磨等,判断是一个聚落就是人口比较多的聚落遗址。另外考古发掘也发现了很多属于唐代的文物,所以年代就确定下来了。然后发掘结果就证实这个城址,就是智城。
智城,位于上林县清水河北岸1.5公里外的一个山间谷地,建造者巧妙利用陡峭的山体作“城墙”,仅在谷地的唯一出口、东南端的两山之间构筑城墙,使不规则的狭长谷地构成了一座封闭、坚固的城池;又在山谷向北转折的狭口处夯筑城墙,使城区分为内城和外城。总体形状呈弯月形,内城面积1.15公顷,外城面积5.04公顷。
《智城碑》位于智城外城入口处25米的东面山脚的崖壁上,为澄州无虞县令韦敬一所制,全文1108字,碑文盛赞了智城及其一带风光形胜;而《大宅颂》位于距离智城4.5公里的圣书大庙的崖洞内,全文381字,是澄州大首领韦敬办所制,碑文赞美了澄州无虞县一处大宅所处地理位置的险要和坚固。那么,这两块唐碑中所描述的“六合坚固大宅”与“智城”有什么关系呢?智城在唐朝时是什么城址处所呢?
广西上林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罗又肄介绍,“六合坚固大宅”,即现在的智城遗址第一道城墙里面的范围。韦敬辨承袭澄州刺史这个职位之后,他也承担他兄弟韦敬办所修的六合坚固大宅,而且把智城的范围往外面扩展。澄州在唐代是一个羁縻州,它的州治基本上就是在智城,管理的范围包括现在的上林、都安、大化、武鸣、宾阳、忻城的一部分。
(广西上林县文物管理所所长 罗又肄)
羁縻制,是秦汉以后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统辖所采取的一种“因俗而治”“以蛮制蛮”的特殊政策。据《新唐书·李靖传》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靖率军征战岭南。之后朝廷开始在岭南划州县,广泛推行羁縻政策。其后,在广西的桂西、桂西南、桂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了50个羁縻州、51个羁縻县。上林所处的澄州便是其中之一,下辖上林、无虞、止戈、贺水四县,而上林就是澄州的州治。
从《大宅颂》、《智城碑》和智城遗址落成的年代来看,它们出现于唐太宗至武则天时期,唐朝的国力逐步兴盛。根据《资治通鉴·卷198》记载,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上林,自古就是壮族聚居地,受到唐太宗“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影响,最终在《大宅颂》碑文中留下了印记。
壮人通过仿照汉字结构来创造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来表达壮语,这些都在《大宅颂》的碑文中有所体现。可见,壮族民间接受汉文字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根据史料记载,初唐时期,中央朝廷就开始在广西不少州县兴办学校。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在岑溪县治东建置学府;贞观元年(627年)建容州府学、博白县学,贞观三年(629年)建北流县学,直接在广西培养人才。
广西师范大学桂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道才介绍,这块碑最惊奇的发现它是用骈文写的。骈文往往是用在朝廷的文书,比如说诏令、下行文。智城碑可以说是一篇把它放在中原跟其他那些作者放一起的时候,毫不逊色的一篇骈文。它是代表了当时的文化的一种先进性,就说它的文风跟中原是并行的;这个作者一定是读过《文选》的。《文选》就是在这之前,是中原文士他们要考科举必须要读的。说明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很早就接受了汉文化。
(广西师范大学桂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道才)
值得注意的是,在《智城碑》中,还出现了武则天时期颁行的六个新造字:日、月、星、天、地、年。《资治通鉴·卷204》有载,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敕令颁布了十二个新字,史称武周改字。时隔八年后,在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刻落的《智城碑》碑文中,就出现了六个新造字,比同样出现武则天新造字的广东省罗定市的《龙龛道场铭》石刻(699年)还早了2年。究竟是什么推动了中原文化向岭南地区的迅速传播呢?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有相思埭,长寿元年筑,分相思水使东西流。”由此可见,在“武周改字”(689年)与《智城碑》(697年)出现的时间轴之间,武则天在长寿元年(692年)的时候,曾修筑了一条相思埭运河。
交通的便利、文人的往来,对传递中央政令和信息的流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岭南文风与中原文风保持同步,中原文化在远离京城的岭南少数民族地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也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交融,不断地融合的,在唐碑里面也得到了印证。要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是个文化共同体,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才有国家的认同。
当岁月长河,从千年以前的盛唐,蜿蜒流转到今天的盛世,沧海桑田间从未改变的是,中华文明与各民族文化相容,根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