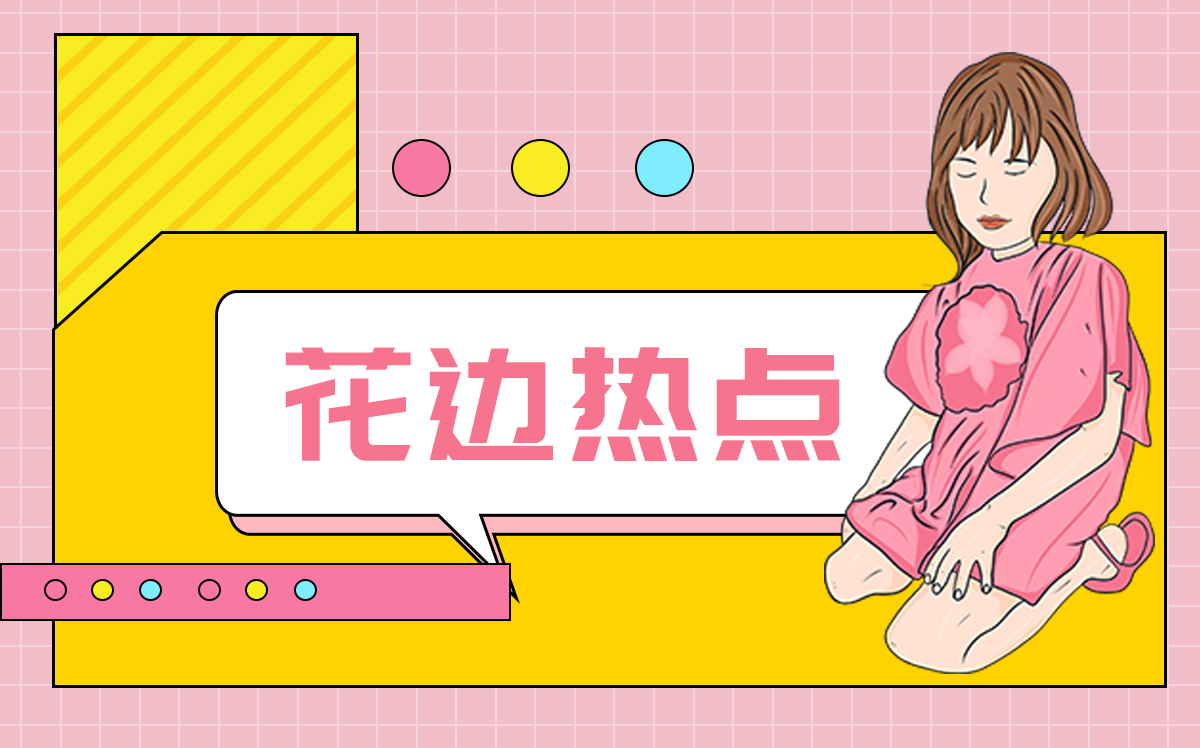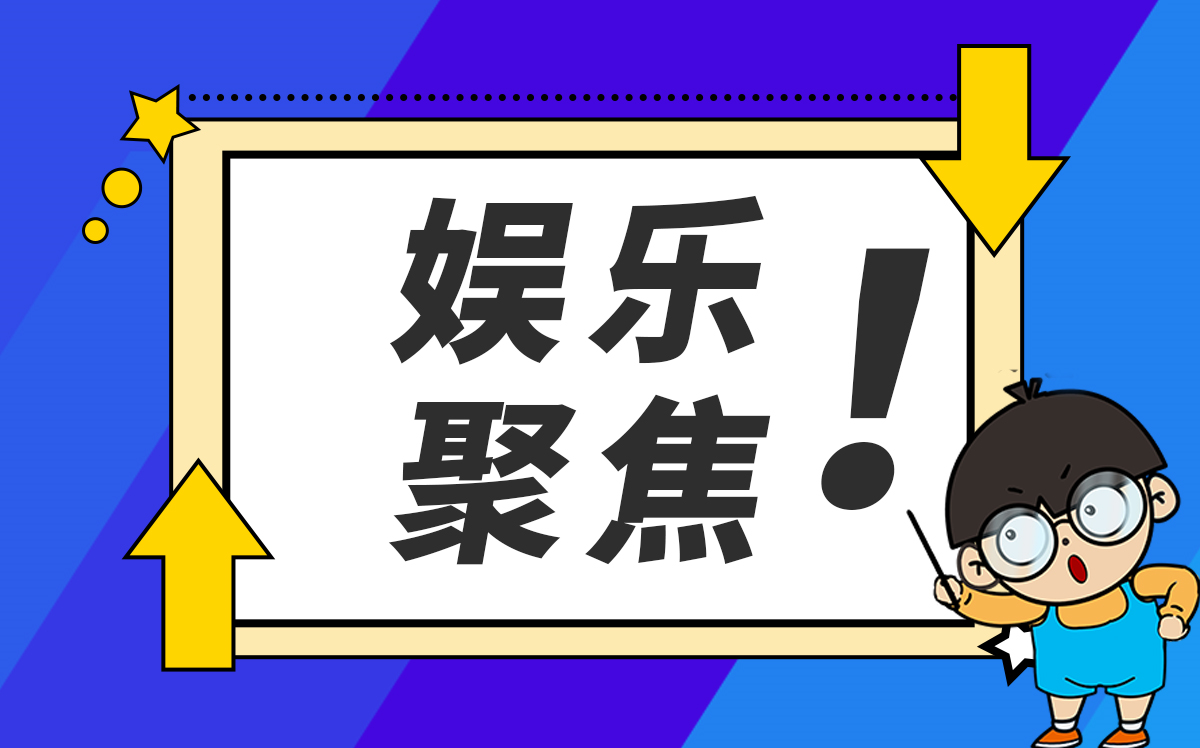何兹全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1911—2011),山东菏泽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7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195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发表学术文章八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史学理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兵制等。
魏晋南北朝历时(公元220—589年)370年,从董卓进京(公元189年),东汉已经名存实亡,到隋朝重新建立大一统的王朝(公元589年)分裂了400年(其中西晋曾有短暂的统一)。正所谓“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段《三国演义》卷首的经典句子,提纲挈领地点明近400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分分合合的典型历史特征。400年的历史,平行或相继的割据政权出现过三十余个,建国者的民族成分极其复杂,在“十六国”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七个民族建立了20多个政权,未建立政权的民族还有很多,如蛮、乌桓、屠各、卢水胡等。人民从北到南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众多民族在碰撞与交融中在历史舞台上纷纷亮相。风云诡谲,英雄辈出。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道教在这一时期深入民众,玄学在这一时期闪现出历史的思想光辉,曾有人因为这一时期的跌宕起伏、曲折迂回,而将之与欧洲大陆的中世纪并称为“黑暗的大陆”。
如何叙述清楚这段历史,如何将这段历史最关键的问题透过的残酷而交织的频繁战争和看似混乱动荡的复杂局面中呈现给研习者,考验着历史学家的见识和思考。
《魏晋南北朝史略》,何兹全 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8月。
虽然这本《史略》篇幅不长,语言浅显,但何先生善于抓住历史主线,善于把握关键问题特点,处处可见“普照一切的光”(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全书有四条主要线索:一是政治之变局;二是民族矛盾与民族融合;三是社会经济变化;四是思想文化的探索。在风诡云谲的动乱中,人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政治领域,经济基础往往容易被忽视。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第三条线索是何先生剖析和把握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特征和变化的核心。
何先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魏晋封建说”,即对社会经济变化的阐述。汉末到两晋南北朝的社会变化,何先生认为应该抓住四条变化主线:一是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二是从自由民、奴隶到依附民;三是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四是从民流到地著。这四条主线的归纳,正体现了何先生把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虽然在这本《史略》中因时代所限,没有明确提出这四条变化主线,但我们仍然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普照一切的光”。我们抓住了这四条主线,也就把握住了这时期社会变化的本质。
秦汉时期,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发达,官府通过统一铸币加以适应和掌控。并施行一系列政策以扶植小自耕农经济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劳动和家内劳动中,权贵和富人也使用大量的奴隶,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是经常发生的,尤其遇到灾年或战乱时期更是如此。西汉后期以后,富商豪强对土地的兼并日趋严重,西汉末年、王莽时期、东汉末年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与土地兼并导致的贫富分化严重、农民破产、被迫流亡等有直接关系。逐渐形成的世家豪族占有大量土地,破产的民众为逃避国家日趋繁重的赋税徭役和战乱,背井离乡,形成大规模的流民。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迅速衰落,自然经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大量的自由民(国家的编户)为生存而成为世家豪族的依附民,人口(即劳动力,徭役和兵役的主要来源)成为各个政权争夺的主要对象,百姓被固着在土地上,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再是国家的编户。国家于是也采取世家豪族的做法,控制土地和劳动人口,三国时期曹魏的屯田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从中看到四条主线的形成和发展。
何先生在分析三国分立的经济基础时指出:“汉末北方经济的衰落和生产力的破坏,使北方的政权一时没有能力统一南方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地方势力,联合起来也只足以自保,还没有能力吞并北方。同时,南方自汉以来,扬州、荆州、益州成为三个经济发展的重心,这种地方性经济的发展,促使政治上的分离而不是促使整个南方的统一。这就决定了整个三国分立的形势。”在分析司马氏取代曹魏上台的社会基础时指出:两种势力的斗争,追根寻源是汉末以来分散性的地方经济发展的结果。在分析东晋立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时指出:一是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一是中原豪族和江南地方豪族的联合力量的拥护。而在分析屯田农的依附性加深时,何先生的四条主线游刃有余地贯穿其中。大江东去也好,刀光剑影也好,轰轰烈烈、万古风流,只有回到对当时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格局的分析上,才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就是何先生给我们昭示的认识历史格局变化的出发点。
如果说秦汉和隋唐是中国古代史发展的两个鼎盛时期,相比隋唐时期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人口的地域性流动和社会性流动逐渐增强的历史格局,魏晋南北朝时期似乎就是中国古代史发展进程呈马鞍形的鞍底。马鞍形的鞍底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古代史发展的低谷,而是社会变化的契机,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反倒融入和呈现丰富多彩的新元素。
何先生的视角继续向后的延伸,被史学界誉为魏晋南北朝史“扛鼎之作”的《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初版),在阐述由“古代到中世纪”的三个变化时,就将此前归纳的四个变化归并为两条线,一是城乡经济的衰落,二是依附关系的发展,增加了第三条:宗教的兴起。他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恰如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文艺复兴时期。虽然在这本《史略》中何先生没有用“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或许这一认识还处在思考时期,也或许是当时的时代局限不适宜做这样的类比。但在注重考察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变化作用的同时,也注重社会意识、思想与之的互动作用。思想方面,《史略》一书并不因为篇幅少,而忽略思想的智慧之光。这一时期是各种思想大碰撞、大交汇时期。魏晋清谈玄学产生的根源,正如何先生在书中所指出的:“汉末清谈的兴起,老庄之学的抬头,曹魏严苛的政治,曹氏司马氏政权的斗争,只能说是助长魏晋清谈玄学产生发展的条件,还不能说是魏晋清谈玄学产生的主要根据。魏晋清谈玄学的所以,应该说是从这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和贵族豪族地主阶级的生活来求得解释。贵族豪族世家是大土地所有者,社会财富都集中在他们手里,腐朽堕落日趋严重,生活实践的腐化堕落,反映到思想意识界,也就必然是腐朽堕落的。而且,腐朽了的贵族阶层也没有能力来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诸多问题,这就决定了他们不敢面向现实,想逃避现实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态度。但他们是土地财富的所有者,是政权的掌握者,又不能离开现实,既不愿自杀,又不能去做和尚,于是走向老庄思想这一道,一方面做官,一方面又清谈讲玄。”何先生分析得很深刻,拨开文化表面的云山雾罩,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仍然是深入到社会经济基础去发掘本质的东西。不铺陈那些玄而又玄的语词,而是直接将读者带进本质的深层。
浅显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的历史,希望读者能从中真正体会作者“对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轮廓、体系、线索的认识”,真正理解作者“对这一时代一些历史问题、历史事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