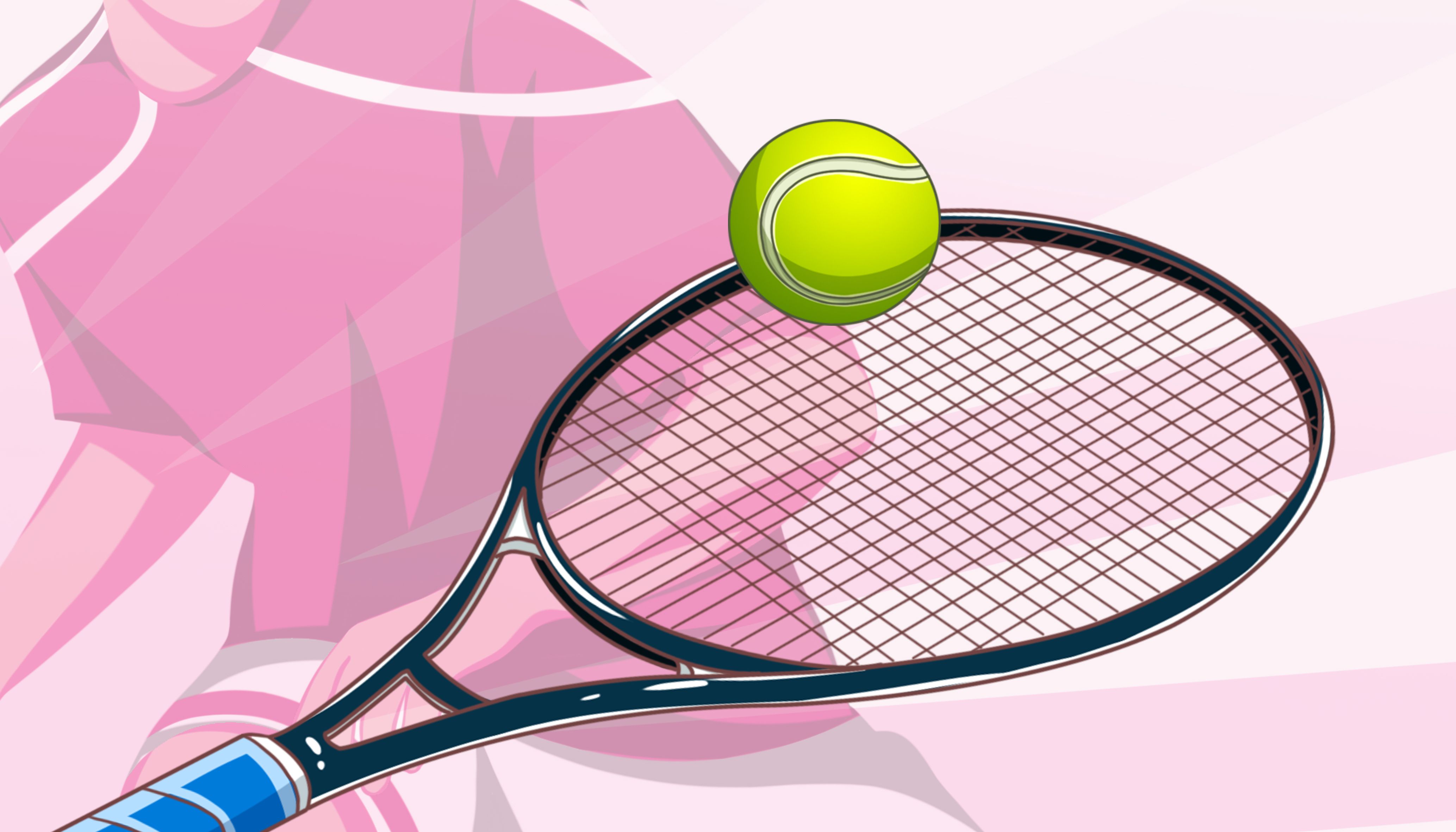新疆有许多被称为“破城子”的遗址,来头最大的恐怕要数吉木萨尔县城北十多公里的一处,这里可是昔日赫赫有名的大唐北庭都护府治所。廿年前便知“北庭”,没想到今日才有缘一谒。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遗址如今被改成考古公园,顺着门房的指引,转过一片丛生杂树,一排排黄色土墙陡然涌入视野,由近及远,像卫士一样默默矗立在萋萋芳草间和茫茫戈壁上。这便是北庭故城了。
故城建于唐初,虽饱受塞外风雨侵蚀和战火破坏,仍能看出当年气象。城墙残高3—5米,宽5—8米,千年岁月沧桑与人事兴衰更替,就湮没在这些残垣断壁之间。
北庭都护府故城(张佳/图)
互成犄角
恰逢阴天,乌云四合,天幕低垂,行走在残垣之下,空气中混合着野草和乱花的清香,四周阒无人声,唯闻鸟语浅唱。戈壁尽头有汽车驶过,卷起一溜长烟,那一刻,时光仿佛凝固。
“都护”一词源于西汉,“都”为全部,“都护”乃“全都监护”之意。千年以来,以“都护”辖西域的,除汉即唐。
汉之经营西域,沿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开辟了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因此设西域都护于天山南麓。唐人则在此基础上,沿天山北麓开辟了丝绸之路新北道,约为从伊吾(今哈密)、经庭州(吉木萨尔)、伊宁到碎叶(约在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一线,根据形势需要,除了在西域故地设立安西都护,又增设北庭都护,主要管辖南起天山、北到阿尔泰山,西抵巴尔喀什湖的广袤地区,以确保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安全。
从地理上看,北庭故城南以天山为屏障,西接轮台(今昌吉古城),北临大漠,往东通过车师道与柳中、交河等重镇相连,是从天山东缓坡进入准噶尔盆地的关键节点,进可攻、退可守,可谓理想的军镇要塞。
而在军事上,天山东、南、北三个方向的唐军此前虽然都受安西都护府节制,但由于地理阻隔,很难做到协同一致。北庭府设置后,与西州(今吐鲁番附近)、安西府形成犄角之势,将本来分散的力量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唐王朝在天山南北的核心防御体系,牢牢拱卫着帝国西部边陲的稳定。
重要的战略地位,注定了北庭命途多舛。在唐王朝力量强盛时,这里是经略边疆、镇抚夷狄的前哨,而一旦长安势弱,这里就成为各方势力觊觎的首要目标。
从公元702年设立,到公元791年最终陷落,在近九十年的时间里,这片土地见证了太多的沉浮、征战与风雨。
北庭都护府形势图(张佳供图/图)
城头不见大唐旗
在一处断壁前,风雨侵蚀的痕迹下,仍能清晰看到夯土的纹路,让人忍不住伸手轻轻触摸。千年以前,这里曾是戍边将士站立的地方。
闭上眼,岁月深处隐隐传来大唐军鼓回响。残阳如血,军旗猎猎,帝国铁骑在漫天风沙中追亡逐北、快意杀伐。当狼烟散尽,敌虏退去,百战余生的将士们就在这城墙下举杯畅饮,醉卧沙场。也有人刚刚接到来自中原的家书,正朝东怅望……
终唐一朝,先后在西域设置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静塞军等多支驻军,这些军队集野战、镇守、屯戍及边防检查等责任于一身,其中瀚海军就驻扎在北庭城中。与其他军队由番、汉构成不同,瀚海军将士主要是关中和中原子弟,来源集中,也是唐王朝在西域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人们总习惯以“盛”来形容唐,这所谓的“盛”,其实是无数将士用肩膀扛起来的。建唐后,帝国边陲一直危机四伏,先是北方的突厥,接下来是西北的突骑施、崛起于中东的阿拉伯帝国,以及西南的吐蕃、南诏等部落。唐王朝为此采取了军事为主、文化为辅的策略,先后设立安东、安西(北庭脱胎于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护府以经略周边。
“安史之乱”爆发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唐王朝国力进入鼎盛时期,唐玄宗的文治武功达到最盛。公元726年,在与吐蕃的大非川之战中,唐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吐蕃势力遂全面退出西域,其他少数民族势力望风臣服。
一时间,“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朝廷也在开远门张贴告示提醒远行者:西极道九千九百里。从长安到碎叶,朝廷号令畅通无阻。
但庙堂之上也有反对声音,认为常年征战使民生凋敝,边将坐大成势,“非国之福也”。不久后,叛乱果然在北部边陲发生,安史叛军势如破竹,兵锋直逼长安。危急时刻,大唐西域诸军入关赴难,其中安西军五千,北庭军七千,这几乎是北庭驻军的全部精锐。
趁着西域空虚,吐蕃人随后卷土重来,攻陷北庭,时任北庭都护赵崇玭在与吐蕃的激战中捐躯。此后,在郭昕、李元忠等名将苦心经营下,唐军虽曾收复北庭,但颓势已不可避免。二十多年后,北庭再度陷落,最后一任北庭都护杨袭古兵败被害,从此北庭城头再不见大唐军旗。
故城遗址的野狐狸(张佳/图)
愁云惨淡万里凝
从断壁处再往前,草丛中惊起一只狐狸,匆匆向深草处跑去。没跑多远,又停下来端坐地上,静静望着来人。
佛狸祠下,神鸦社鼓,所有风流总逃不过雨打风吹。
关于兴衰更替,唐人也有自己的感怀。从李太白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到刘梦得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再到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他们的感慨从怀古忧今,逐步变得充满哲学思考。
时光流转,兴衰更替,但总有一些人事被历史所铭记。在北庭,除了马背上的赫赫战功,最为人所熟知的当非岑嘉州莫属。
岑嘉州以边塞诗雄踞大唐诗坛,他的诗风雄浑壮丽,既充满了慷慨豪情,又将戍边艰辛与将士们的精神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送武判官归京所做的白雪歌,堪称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其中“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后半句意境,与当日何其相似。
诗作源于生活。岑嘉州一生两赴西域,都是担任名将封常清的幕僚,第二次是在公元754年,封常清从安西转调北庭伊西节度使,他受邀赴北庭任节度判官,那些边塞诗中的名篇,大都作于这一时期。
这段历史在考古界也得到印证。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一具纸糊的棺材,上面载有一笔马料出入账:“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三斗伍升付健儿陈金”,据考此处的“岑判官”即为岑参。千年桑田沧海,多少英雄豪杰都湮没于历史尘沙,唯有诗、书不灭。
梳理他的边塞诗,许多都作于送别时或旅途中。“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这是他在武威送刘判官;“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这是他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饮;“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是他托使者带给长安家人的话;“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这是他途经大漠时的感慨……
岑嘉州的诗兼具豪迈、乐观与苍凉意境,这与他的家世和抱负不无关系。岑氏本是豪门,他的曾祖父岑文本乃太宗朝名相,无奈到他早已家道中落,他肩负着重振家族的重任。
可惜生不逢时,玄宗一心用武力除戎患、吞四夷,寻章摘句无非老弱雕虫。因此他只能投身军旅,希望在边塞建立功勋,这从他757年的一篇诗作中可以看出:
北庭作
雁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
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在众多作品中,这是少有的透出感伤之情的。作此篇后,他随北庭平叛大军东入玉门,不久回到长安。八年之后被贬嘉州,随后又在兵荒马乱的蜀中经历了四年的颠沛流离,一代诗雄最后客死成都。
少年虚负凌云志,一生襟抱终未开。在困居蜀中的日子里,边塞的铁马冰河、胡歌羌笛,不知会不会时常进入他的梦里。
故城遗存(张佳/图)
佛狸祠下,神鸦社鼓
紧邻北庭故城遗址西侧,建有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馆,内中保护着一座回鹘王家佛寺,当地人俗称其为“西大寺”。佛寺残高约十多米,站在博物馆三层可窥全貌,经考古人员发掘规整,依稀能看出昔日布局。
王家佛寺与北庭故城相邻,颇耐人寻味。与唐王朝开放包容的气度一样,唐人在经略西域时也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唐将士为多元文化创造出和平发展环境,在他们庇护下,佛教、景教、拜火教等多种宗教蓬勃发展,西域文化达到历史上的巅峰时期。回鹘即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在该民族的历史上,先后信奉过萨满、摩尼、佛教等宗教,是不争的事实。
可惜随着北庭、安西先后陷落,中原王朝势力渐次退出西域,此前汉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保持多年的平衡被打破,伊斯兰教趁虚东扩。后来几经演变,西域多种宗教共同繁荣的局面被打破,最终变成了伊斯兰教一枝独秀。
博物馆里的佛教壁画(张佳/图)
博物馆中除了佛寺遗址,还保存着出土的佛像和佛教壁画。与敦煌莫高窟乃至新疆各地的千佛洞相比,这昔日的王家佛寺不但名头逊色许多,在规模上也略显落魄。
名气不大,既是一种不幸,又是一种幸运。不幸的是,千年前的盛世繁华,如今零落殆尽,但也正因为名气不大,才得以最大限度保全。
在博物馆一楼大厅的展板上,展示着《北庭史丛集》《瀚海天山》等著作封面,那是北庭研究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他们既是北庭的研究者,也是守护者。
公路上的北庭故城指示牌(张佳/图)
走出博物馆,门前蔷薇怒放,当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正在拍摄视频,“要做一期关于‘丝绸之路’的文化片”。摄像机显示屏上,天空乌云快速翻转,“北庭故城”杏黄小旗在馆顶迎风招展。
回首东望,苍穹之下,北庭故城重又被掩映在岁月深处。
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