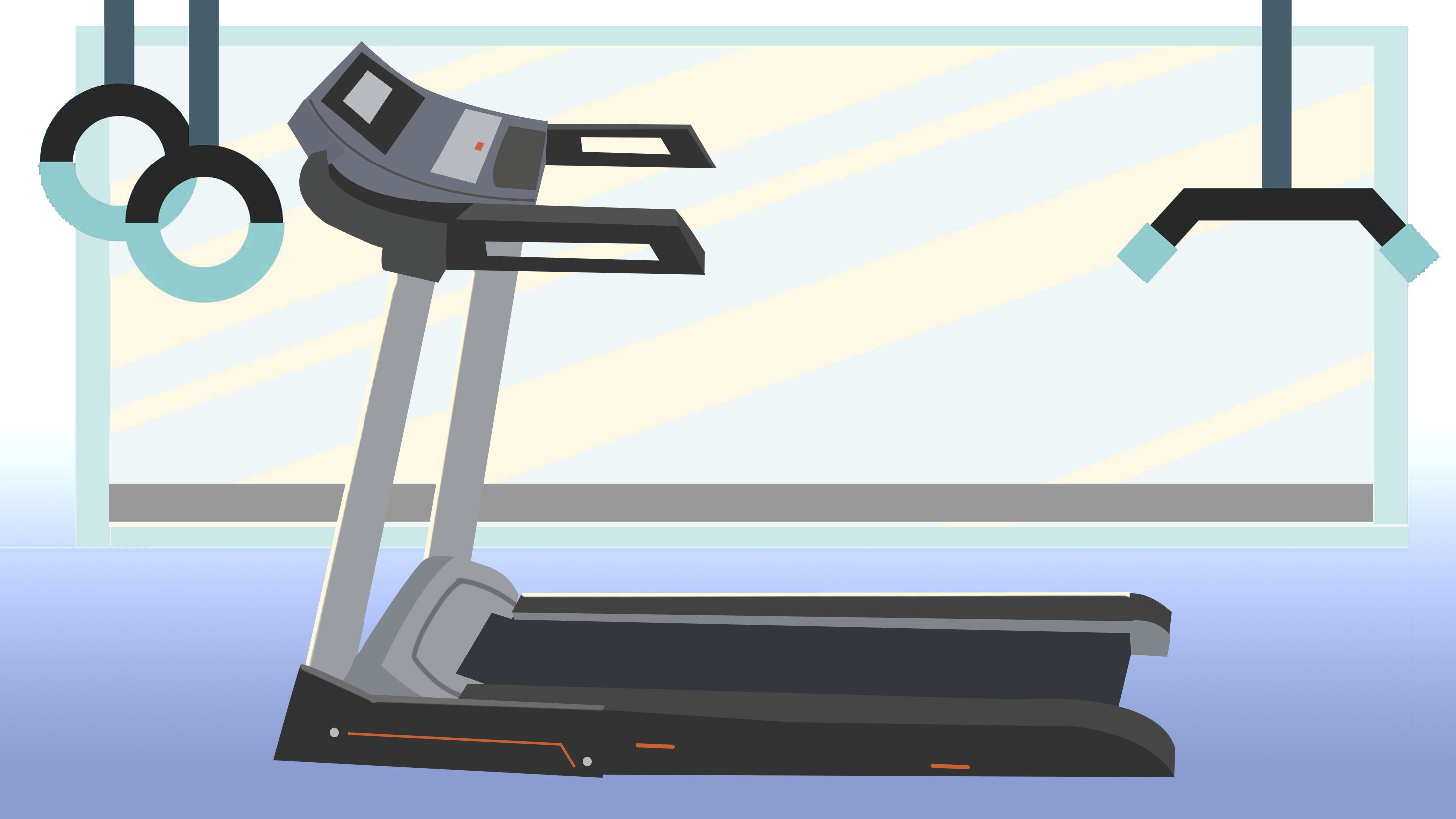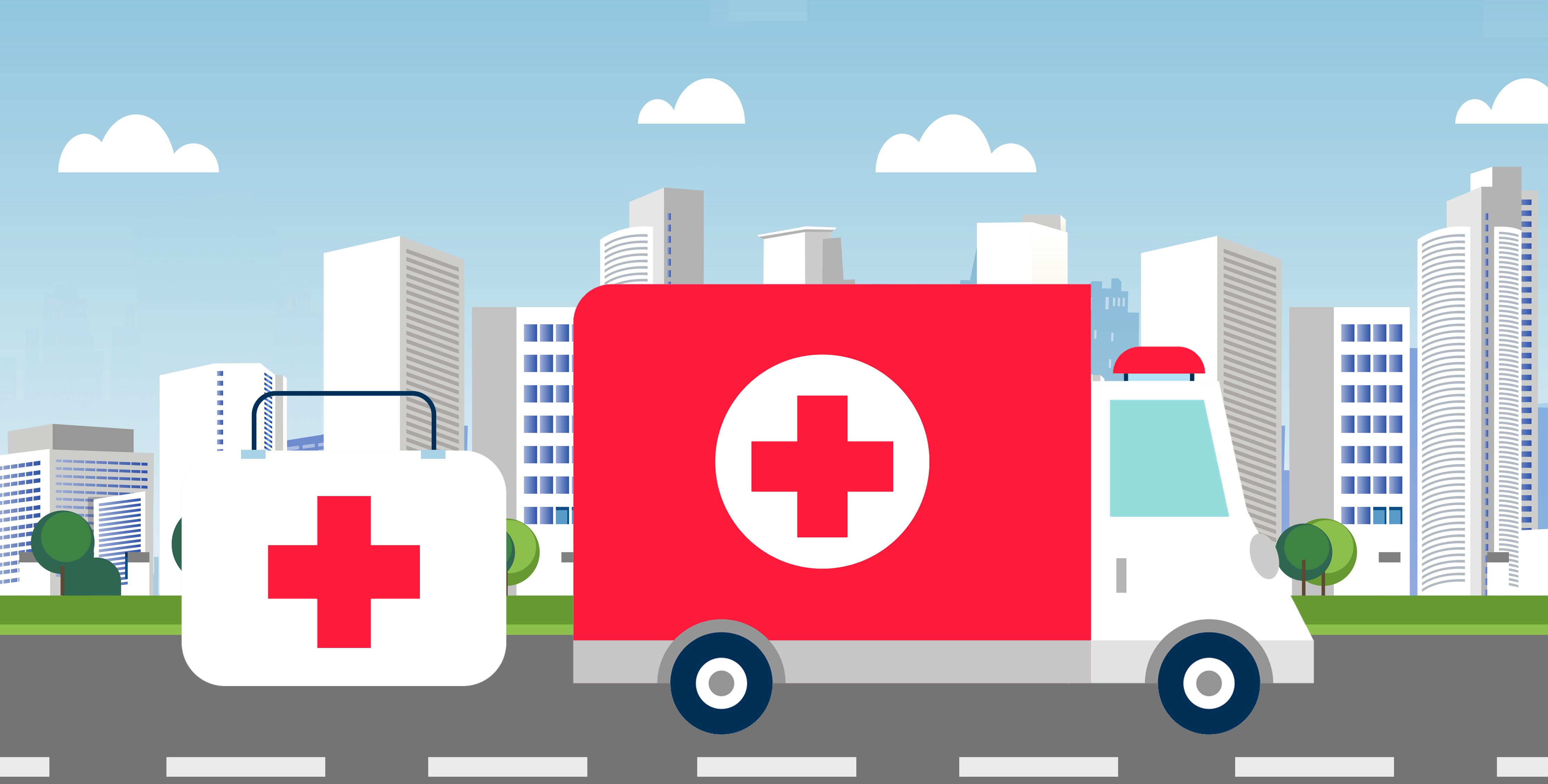摘要:楚雄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在明代之前,儒家文化对其影响有限。明代主要以流官群体治理楚雄,儒学教育得以开展和推广。清代更加注重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继续推广和传播儒学教育。一是恢复或修葺明代建立的各级宫学,并广开资金来源渠道;二是启蒙教育机构——义学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三是书院在明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代儒学教育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而且在夷汉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方面影响甚巨。
关键词:清代;楚雄地区;儒学教育;民族融合;文化交融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楚雄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云南地区已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作为汉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至迟在东汉时已传入云南。然而,在中央实施羁縻治策和土司制度,或云南割据一方的情况下,儒学对包括楚雄在内的云南地区影响有限。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蛮文云‘保和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1]
有明一代,随着郡县制和改土归流的运行和实施,儒学教育也在楚雄地区得到广泛传播,使古蛮夷之地“人才崛起,屡中甲科”,促进了汉夷之间的文化交融。清政府承继了明代儒学教化的治边之道,更加重视儒学教育的推广。
一、儒学教育的传播
明清鼎革,清王朝对明代治边之策多有承继,其中就包括“尊孔读经”的文教政策。平定“三藩之乱”后,云贵首任总督蔡毓荣就认为:“从来地方,在风俗;风俗之后,在教化;教化之兴,在诗书,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上之人加之意耳。”[2]明代楚雄地区各府州县所建学宫,历经自然界的风雨和改朝换代的战火,到康熙年间大多破败不堪了。清代各府州县儒学一般是在明代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见表1)。
表1 清代楚雄地区重修府州县学宫一览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在楚雄、武定等八府,楚雄县、定远县、和曲州、姚州等十七州县儒学各设训导一员,此为清代数量最大、时间最集中的一次学校设置。
清代儒学教育系统的重建,虽由地方主要行政官员,如知府、知州、知县主持,但办学资金来源却是多方筹措的,主要包括财政拨款、士绅捐助和学田三部分。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建白盐井儒学,“除奉拨十一年分归公门随银二百三十二两外,贡生罗铨乐捐银一百两,五井士杜乐捐银二百四十三两三钱四分五厘九毫四丝”,地方士绅捐赠成为经费来源大宗。
不仅如此,儒学教育若想长期健康存续,必须稳定其经费来源,而学田的建立和维护是主要举措。白井文庙建于万历年间,“历任父师虽间有修葺之处,不过补偏救敝,既无学田以为修补之资,日久年深,木植腐朽,迟延至今,尽为倾颓废”。因而白井生员陈斗光,“情愿将父遗柳树塘田一分,递年收租谷价值百金永入学宫,以为将来修葺之费。若有余剩谷石,或学中有志上进无父兄供给者,将此项租谷给与以助膏火”[3]。
如果说元代的云南儒学是生长,明代是扎根的话,那么清代的云南府州县儒学则向纵深发展,是时云南人才辈出,儒学之盛洋洋大观,内地儒学和儒学思想已经僵化,已是穷途末路,而在云南则方兴未艾。[4]
二、义学教育的开展
明代的启蒙教育机构,一般称为社学;到清代,对贫寒子弟进行启蒙及初等教育的机构,则被称为义学。康熙时南安州知州张伦至称:“我朝于郡州县皆建学,所以籍士之秀者,潜裕敏给,以一其情于仁义礼乐之具,而恣之成以仕,可谓盛矣。至于乡闾有塾,择贤有德为之师。问之,此地间有而或无也,则义学之设诚亟已。”[5]义学招生没有学生数量限制,也不需要经过考试,只要在孔子牌位前和塾师前行跪拜叩首礼,即可成为义学学生。义学负有德化的使命,道德教育的内容渗透在识字、习字、学诗、作文、读史、学经等各类教材之中。同时还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或应科举考试做准备。
“三藩之乱”平定后,云贵总督蔡毓荣就建义学、兴教化上疏:“滇人陷溺数年,所见习者皆灭理乱常之事,几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矣!今既如长夜之复旦,反经定志,全在此时。臣已饬行有司各设义学,教其子弟,各以朔望讲约,阐扬圣谕,以感动其天良。各选年高有德之人,给以月廪,风示乡里,但人情率始勤而终怠,其或作辍不常,安能久道化成而保民无邪慝耶?则所以革民心,兴民行者之力行宜亟也。”[6]蔡毓荣兴建义学之议得到了批准。在云南布政司、楚雄府两级政府的督办下,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二十九年(1690年),不到10年的时间,楚雄地区即建起了21所义学(见表2)。
表2 康熙年间楚雄地区义学一览
续表2:
资料来源:《古今图书集成》第一七八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八十卷《楚雄府部汇考二·楚雄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8-9页;第一七九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九十七卷《姚安府部汇考一·姚安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25-26页;第一七九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五百一卷《武定府部汇考一·武定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48页。康熙《镇南州志》卷二《学校》,《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南华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表2显示,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楚雄地区共建义学23所,其中楚雄府最多,共有12所。从设立时间上来看,最早设立的两所分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设立的定远县义学和二十二年(1683年)设立的镇南州义学,两者甚至比楚雄府主持设立的府义学还要早7~9年。有学者根据康熙《云南通志》所载,统计出康熙年间云南共设立义学139所。①若楚雄府就有23所的话,那么139所的总量则显得过于保守了。
如果说康熙年间是云南义学初步发轫的时期,那么雍正、乾隆年间则是云南义学充分发展的时期。雍正继位后,对云南省情也有深刻认知:“云南等省所有苗蛮种类甚多……朕亦不忍听其独在德化之外,是亦从封疆大臣之请,剿抚兼行,而切加训诲,务以化导招徕为本,不可胁以兵武。”[7]力行教化、德化成为先于兵武的治滇之策,而要达此目的,兴办义学、多加训诲则是必然之路。雍正十一年(1733年),陈宏谋任云南布政使,成为云南义学发展的开拓者。
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雍正元年(1723年),举乡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乾隆二年(1737年),陈氏经过细致调研,撰写了《查建义学檄》,提出“兴学为变俗之方”的理念,决意要多设义学。②“义学宜城市与乡村并设”,除了保留以前在城内所设的义学外,陈宏谋力主将义学更多地建在乡村边远地区。为确保义学在云南的发展,陈宏谋特别拟定了《义学条规议》,以保证义学能够持续正常运行。对于陈氏兴建义学之功,《清史稿》称:“十一年,擢云南布政使,立义学七百余所,令苗民得就学,教之书。刻孝经、小学及所辑纲鉴、大学衍义,分布各属。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8]
此后,云南总督张允随亦对义学重视有加。乾隆九年(1744年),张允随奏称:“滇省蛮夷之性,虽云犷野,而朴直无欺,结以恩信,咸知感格,时时勉励各属,躬行倡导。现在夷方倮族,亦解好施,爨女蛮媛,渐知守志;并增建义学三百七十余所,捐置田亩,以充馆谷;选择师儒,以司训课。现在肄业诸生中,不乏笃学好修之士。此教民各条之实事也。”[9]
在各级官员的努力下,义学亦很快在楚雄地区发展起来。丁存金根据《新纂云南通志》,计算出清代云南共举办义学827所,而楚雄地区为122所,后者占全省数量的14.75%,具体数目见表3。
表3 清代云南省志中所载楚雄地区的义学数目一览 单位:所
资料来源:丁存金:《清代云南义学的发展和演变》附表,《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1期。
表3显示,康熙时期是云南义学初步发展的阶段,彼时楚雄地区的义学也有较大发展,其数量占云南全省的15%。雍正在位期间(1723—1735年)是清代云南义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13年,然而云南义学数量却有跨越式发展。康熙时期云南义学数量只有120所,雍正年间增加了405所。而楚雄地区义学的数量,也从18所增加了73所。而根据前文论述,云南义学发展的最好时期应该是乾隆年间。因为无论是陈宏谋,还是张允随,其主政云南、力推义学的时段均为乾隆年间,而非雍正年间。前者执政期间“立义学七百余所”,而后者亦“增建义学三百七十余所”,可惜没有遗存文献刊载。嘉庆之后直至清末,楚雄地区乃至云南省义学处于停滞或衰退的状态。
义学是一种基础性初等教育,若要维持或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必须解决好经费问题。学田是义学经费的稳定来源。广通县义学是在明社学旧址上建成的,岁入租成为办学经费。③元谋县“义学地一块,每年收高粱租市石五石三,充教习薪水”[10]。有的地方学田不足,政府官员就需要设法拨给一些田产。④
由于政策、经费得到保证,义学在楚雄地区有了长足发展。有的义学由明代社学改建而来,如嘉县社学日久已废,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在城隍祠重建。[11]有的义学后来则发展为书院,如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南安州山天书院,是由于两年前所建义学“地促屋少,不能多集生童”扩建而来[12]。清代云南基础教育的扩展,就使少数民族子弟接受儒学教育的比例逐渐增高。康熙年间元谋知县由衷感叹,“僻壤荒陬,无不敦诗书而尚礼乐”[13]。
三、书院讲学的兴盛
清代义学正如明代社学,皆属于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之范畴,而书院则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今夫育才之所有二,曰学校,曰书院。学校为士子习礼之地,而书院在讲肄之所聚也”[14]。书院的学生都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能入学。书院也是义学学生深造的地方。为鼓励学生上进,陈宏谋曾规定可以为义学经馆中的成材学员提供便利,经考试后到书院读书。清代云南书院以科举考试为主要目标,讲学之风荡然无存。
顺治年间,鉴于明末东林党影响之巨,清政府对思想言论控制甚严,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但因书院制度历经宋、元、明涵泳,盘根错节,影响至深,清政令虽严,然禁而不止。康熙当政后,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欣赏态度,亦允许书院聚徒讲学,并手书“学达性天”匾额赐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
清代楚雄第一批书院是在明代书院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不过有的是在原址重建,如定远县嘉靖时所建文龙书院,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由知县袁乃湔捐脩重建。[15]有的是恢复原有书院的名称,但另外选址,如大姚县的文明书院、楚雄府的龙泉书院。有的则纯粹为新建书院,如镇南州明代并无书院,清代新建龙川书院。此书院在学宫东,濒临龙川江,嘉庆十七年(1812年)由知州苏世勋等倡建,“规制宏敞,栋宇磈叠,榜曰龙川,义取龙川江之所发源也”[16]。龙川江为金沙江支流,发源于镇南州,即以此而取名。
选址重建或新建书院,所需费用较多,首先得筹集建校经费。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楚雄知府卢洵于府城西学旧址,捐俸起建明伦堂三间,左右书舍各五间,大门三楹,为诸生肄业之所。嘉庆时苏世勋所建龙川书院,因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而毁于战火中。光绪十一年(1893年),蜀人蔡之模任云南镇南州知州,以“差徭”费用,移做龙川书院重修经费,并自捐“俸金五十两”[17],最终龙川书院得以重建。可见,官员捐俸,不仅是兴办义学的经费来源,举办书院也是如此。甚至挪用公款,也能成为书院成败的关键。
与明代相比,清代官员兴办书院的热情更高,成就自然也更大。表4列示了清代楚雄地区所建书院的情况。
表4显示,清代楚雄地区建有书院35所,而明代书院只有11所,清代书院的数量是明代的3倍多,可见清代楚雄地区书院之盛。对照两表可知,明代黑盐井、白盐井和琅盐井三提举司并无书院之设,而清代三提举司不仅取得零的突破,而且所建书院达到8所。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盛况,当然与清政府大力提倡,地方官员有所作为有关。然而对三提举司来说,人文荟萃、书院勃兴更多的是由于盐业经济兴盛所引致。
楚雄地区书院初创时,主要依靠热心教育的士绅及民众的捐款、捐租,这与义学创办主要靠官员捐俸有所不同。而在书院存续和发展的过程中,学田所起的作用是首屈一指的。
清末一些书院改为学堂,近代教育开始建立起来。如龙泉书院,原名雁峰书院,在楚雄县,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书院改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知府崇谦以中学堂为七属荟萃之所,改在学使考棚,将龙泉书院拨归楚雄县为高等小学;宣统二年(1910年),“学生除送府送省外,陆续添入共百余名,分甲乙丙三班”。[18]又如白盐井龙吟书院,亦于光绪三十年改为高等小学堂。清末书院成为创建近代学堂的基础,对于近代楚雄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其作用不可抹杀。
表4 清代楚雄地区书院一览表
资料来源: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六)》卷一三五《学制考五》统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6-561、593-597页。另据道光《姚州志》卷二《学校》,《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273页;《古今图书集成》第一七八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八十卷《楚雄府部汇考二·楚雄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8-9页增补。
四、儒学传播对楚雄地区的影响
作为多民族杂居之地,历史上楚雄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较之内地均有所不及。明太祖认为风淳俗美,国易为治,从而彰显教化,因而秉持“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主”的治边理念。清朝秉持“尊孔读经”的理念,教化成为创办各级儒学、社学、义学、书院等所有教育机构的目的。明清儒学在楚雄地区的传播,在人才培养、文化融合等方面对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是儒学教育大发展的时期,根据李中清研究,1750-1850年的100年里,有70多个少数民族人士考中了进士或状元,此数略3倍于1350-1750年共400年间考上总数。[19]楚雄地区也是如此,考中进士者达到38人,是明代10人的3.8倍。具体内容见表5。
表5 清代楚雄地区进士分布表
资料来源: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明代云南、临安、大理、永昌和鹤庆五府所出人才最多,五府进士216人,占明代全省进士总数的82.18%;清朝云南、临安、大理、澄江、楚雄五府所出人才最多,五府进士550人,占清代全省进士的80.15%,[20]楚雄地区的进士数量进入了全省前五名。从朝代分布来看,嘉庆年间楚雄地区中进士者最多,共10人,占云南进士总数的8.62%。清代姚州在明代四进士的基础上,雍乾年间继续科举连发,樊仲琇、甘美、李天骏、饶有亮成为新的四进士[21]。明代元谋一县,未曾出过进士;然这一局面在清初被陈时夏改变了。陈氏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为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科进士,后补内阁中书,历任湖北按察使、江苏巡抚、山东布政使,《清史稿》卷二九三有其传记。
清代楚雄书院亦为科举考试输送了大量人才,表6列示了部分书院培养的人才名录,其中黑盐井提举司的龙江书院表现尤为优异。
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来到楚雄地区,原来“夷多汉少”的状况已发生了较大改变。人才蔚起,出为国桢,“曲靖、楚雄、姚安、澄江之间,山川夷旷,民富足而生礼仪,人文日益兴起”。[22]其中名声最著者是明末姚安府的陶珽、陶珙兄弟和清初学术大师高奣映。
陶珽,字紫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交游广泛,与袁宏道、董其昌、陈继儒等文坛领袖时有诗文唱和。其著述丰富,以《说郛续》流传最广。陶珙,字紫阎,陶珽之弟,天启初举人,有《寄园集》传留后世。此后高奣映继起,著书七十九种,凡经史释老、天文舆地、文学诗词,均有著作诠解。高奣映(1647-1707),字雪君,清初姚安府土同知。姚安高氏是明清时期受汉文化影响至深的土司,在传播汉文化、提携后学方面成绩斐然。清人谓,“清初诸儒,应以顾、黄、王、颜、高五氏并列,非过论也”,而高氏“及门之士,成进士者二十二人,登乡荐者四十七人”。[23]
表6 清代楚雄地区部分书院培养的人才统计
资料来源:云南省图书馆藏《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旧日书院资料》,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抄本,转引自肖雄《明清云南书院与边疆文化教育发展研究》表5-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在文化交融的基础上,民族融合也有了进一步加强。明代之前的“汉夷”民族关系,其表现是汉族不断融入少数民族文化之中。彼时楚雄地区处于比较初级的社会形态,没有自觉接受儒家文化的基础。因而不论何种原因进入的汉民,因其人口较少,只能“变服从其俗”,接受“夷化”。明清时期各级学校的举办,儒学的广泛传播,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通过“德化”或“教化”,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汉化”,其日常礼仪、行为规范等,逐渐统一到正统的儒学文化体系中。从“夷化”到“汉化”的过程,是与儒学教育的推广与传播相一致的。
清代的义学不同于府州县的儒学和书院,主要承担初等教育的功能,不以为国家输送科举人才为目的,因而直接引发了教育平民化的趋势。无论学宫、书院还是义学,授课语言均是汉语,课文均用汉字书写。少数民族儒学启蒙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先通汉音,渐识汉字”。姚安府为“汉夷”杂居区,社学设立之后,该地出现了“用夏变夷……以敷文教”“文教之盛,猗欤休哉”的状况。白盐井民“莫不沐浴圣化,习礼让而安升业”[24]。
从维护边疆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角度看,在边疆民族地区兴办官办各类学校,普及汉文化,是清朝维护边疆统一安定,加速边疆社会进步和文明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虽然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教化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汉夷”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注释:
① 于晓燕:《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统计康熙时云南义学共有139所。
② 雍正《云南通志》卷二九《艺文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584页载:“滇南越在遐荒,夷多汉少,土田硗瘠,居民穷苦,多有俊秀子弟,苦于无力延师;又夷俗不事诗书,罔知礼法,急当诱掖奖劝,俾其向学亲师,熏陶渐染,以化其鄙野强悍之习。是义学之设,文化风俗所系,在滇省尤为紧要也……但查各属从前义学,或止为成材而设,而蒙童小子未能广行教读。或止设在城中,便于附近汉人子弟,而乡村夷倮,未能多设义师。蒙养为圣功之始,则教小子尤急于教成人;兴学为变俗之方,则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今欲使成人、小子、汉人、夷人不以家贫而废学,不以地僻而无师,非多设义学不可。”《培远堂文檄》卷三《通省义学规条详》亦载:“边土之义学,视中土尤宜,而乡村夷寨之义学,较城市尤急,边土贫寒,力能延师者寡,至于乡村夷寨,刀耕火种,力食不暇,何有诗书无惑乎?”
③ 《古今图书集成》第一七八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八十卷《楚雄府部汇考二·楚雄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8页称“其旧租岁入米约三十石,岁纳粮一石七斗,岁入租除交粮捐赈贫生外,额存银七两二钱七分三厘解提学道”。
④道光《定远县志》卷二《学校》,《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牟定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154页载:“明时,士民捐输义田一顷八十八亩三分,又地九十一亩七分六厘,大小十五块。雍正十三年,知县马公德至查清,归入义学。”
参考文献:
[1] 李京著,王叔武校.云南志略辑校[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88.
[2] 蔡毓荣.新建昆明书院碑记[C]//新纂云南通志(六)·卷一三四[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528.
[3] 刘邦瑞.捐置学田碑记[C]//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八.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869.
[4] 木芹,木霁.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232.
[5] 张伦至.南安州义学记[C]//康熙南安州志·卷六.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双柏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67.
[6] 蔡毓荣.筹滇十疏[C]//雍正云南通志·卷二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81.
[7]云南通志·卷二九[Z]//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16-317.
[8] 清史稿·卷三〇七[Z].北京:中华书局,1977:10558.
[9]清实录·高宗实录·二二九[Z].北京:中华书局,1985:962-963.
[10] 元谋县志·卷三[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元谋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51.
[11] 南安州志·卷三[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双柏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26.
[12] 南安州志·卷六[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双柏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71.
[13]元谋县志·卷四[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元谋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39.
[14] 续修白盐井志·卷八[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873.
[15]定远县志·卷二[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牟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7.
[16] 镇南州志略·卷三[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南华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463.
[17]镇南州志略·卷一〇[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南华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463-464.
[18] 楚雄县志·卷三[Z]//中国方志丛书·第3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49.
[19] 李中清.一二五〇年——一八五〇年西南移民史[J].社会科学战线,1983(1):125.
[20] 侯峰,罗朝新.明清云南人才的地理分布[J].学术探索,2002(1):87-90.
[21] 姚州志·卷三[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66.
[22] 谢肇淛.滇略·卷四[Z]//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41.
[23] 姚安县志·第五册·学术志[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646.
[24] 白盐井志·卷一[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421-422.
作者简介:侯官响,男,山东临沂人,楚雄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史、地方文化研究。原载于《文山学院学报》 2020年第2期。
说明: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平台《 滇史》,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联系管理删除。云南松稞商业有限公司旗下松稞茶业,专注于云南普洱古树茶私人订制、礼品包装定制、古茶树认购认养、茶山游等业务,欢迎骚扰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