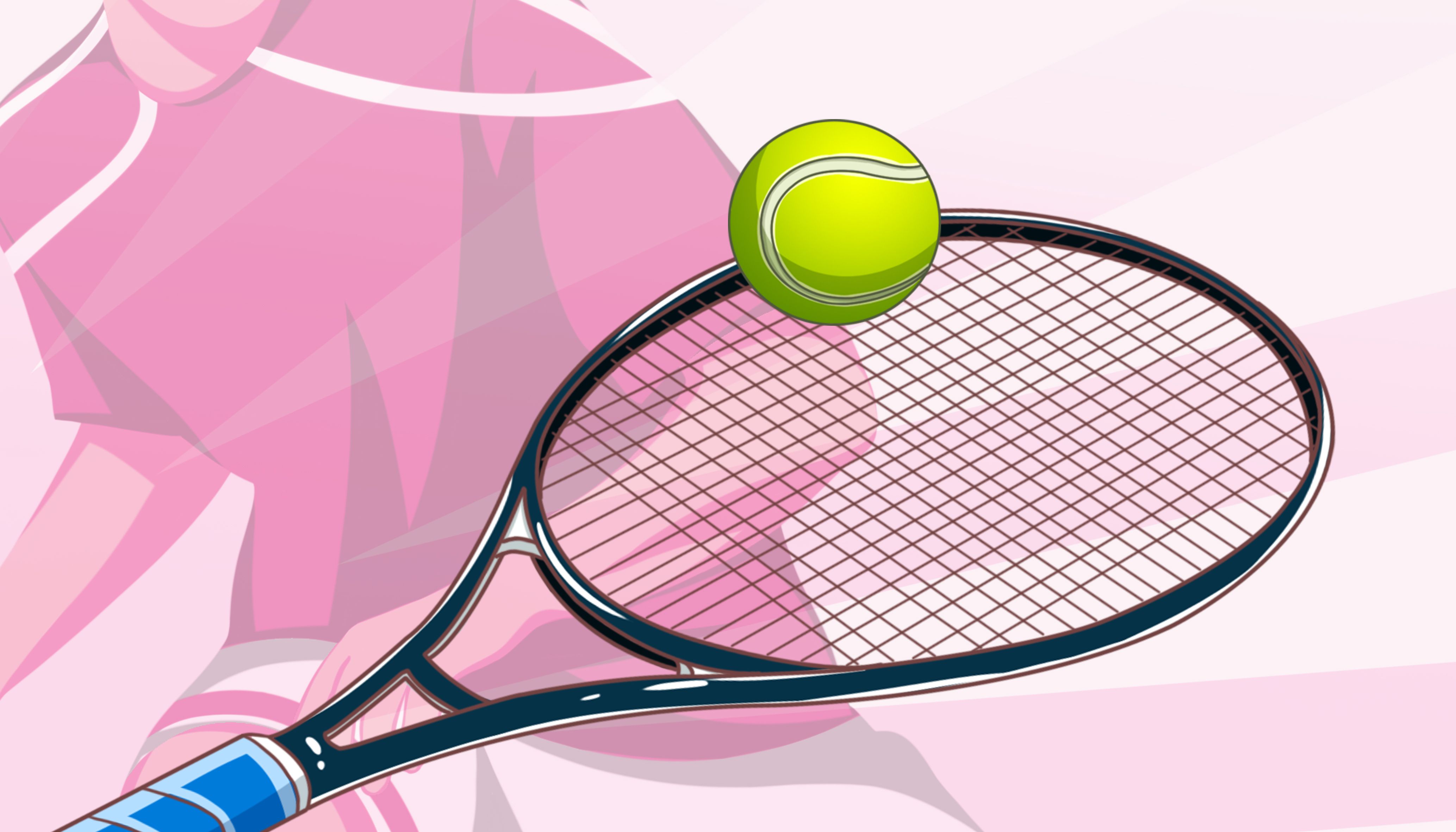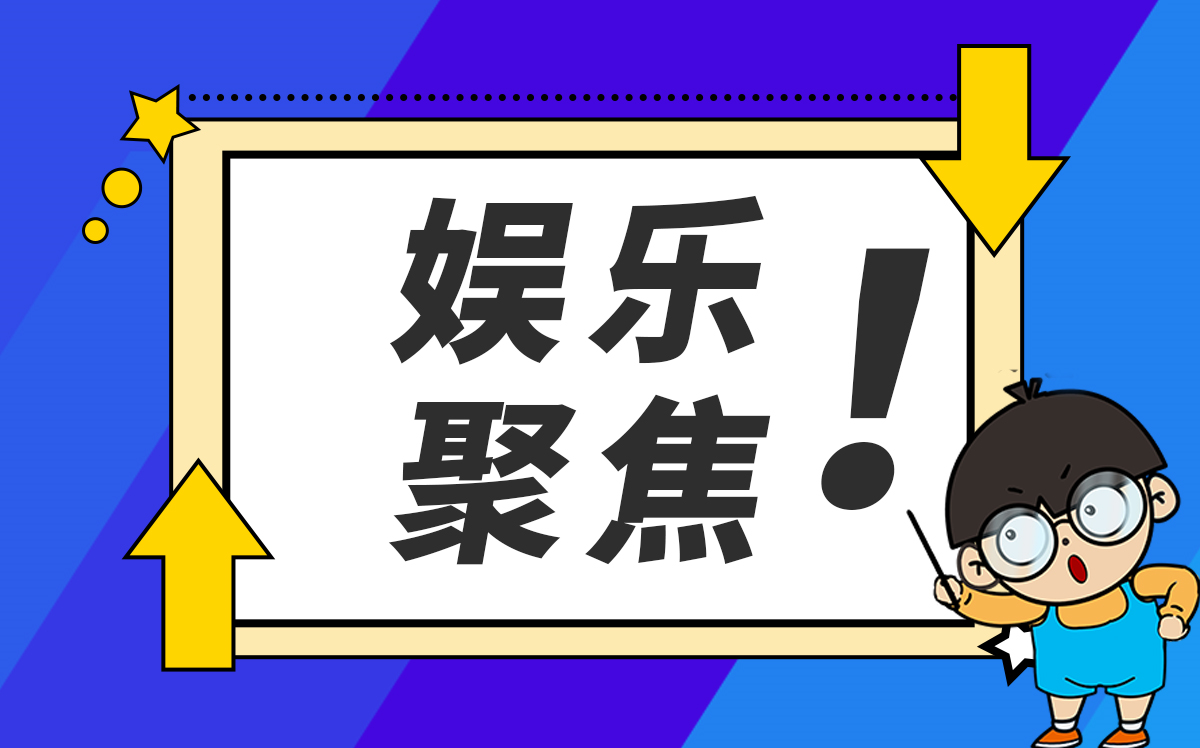提起中国古代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大众最熟悉的。其实,除汉武帝外,其他几个皇帝在贵州的影响都不算很大。明太祖朱元璋是对贵州历史影响相对较大的一个,他的许多举措,至今还留有不少历史烙印。此外,清代前期康、雍、乾三位帝王的治黔方略,不仅对贵州的历史进程造成了明显的影响,而且对清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以及贵州状况的改变都关系密切。
清军在消灭南明永历小王朝后占领了贵州,但所面临的是一种政治上动荡、经济上闭塞落后、交织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残破局面。为了牢固确立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安定西南边疆,清代前期的统治者不能不认真考虑一套有别于内地的治黔方略,并推出一系列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得失兼有,利弊掺杂,从历史发展的视野进行考察,不仅针对性强,收效也很明显。
清初治黔,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着重稳定政局,统一行政区划,继之以恢复发展社会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策的倾斜度有所不同。大体说来,顺(治)、康(熙)年间属第一阶段,从雍正元年(1723年)起至乾隆末,可视为第二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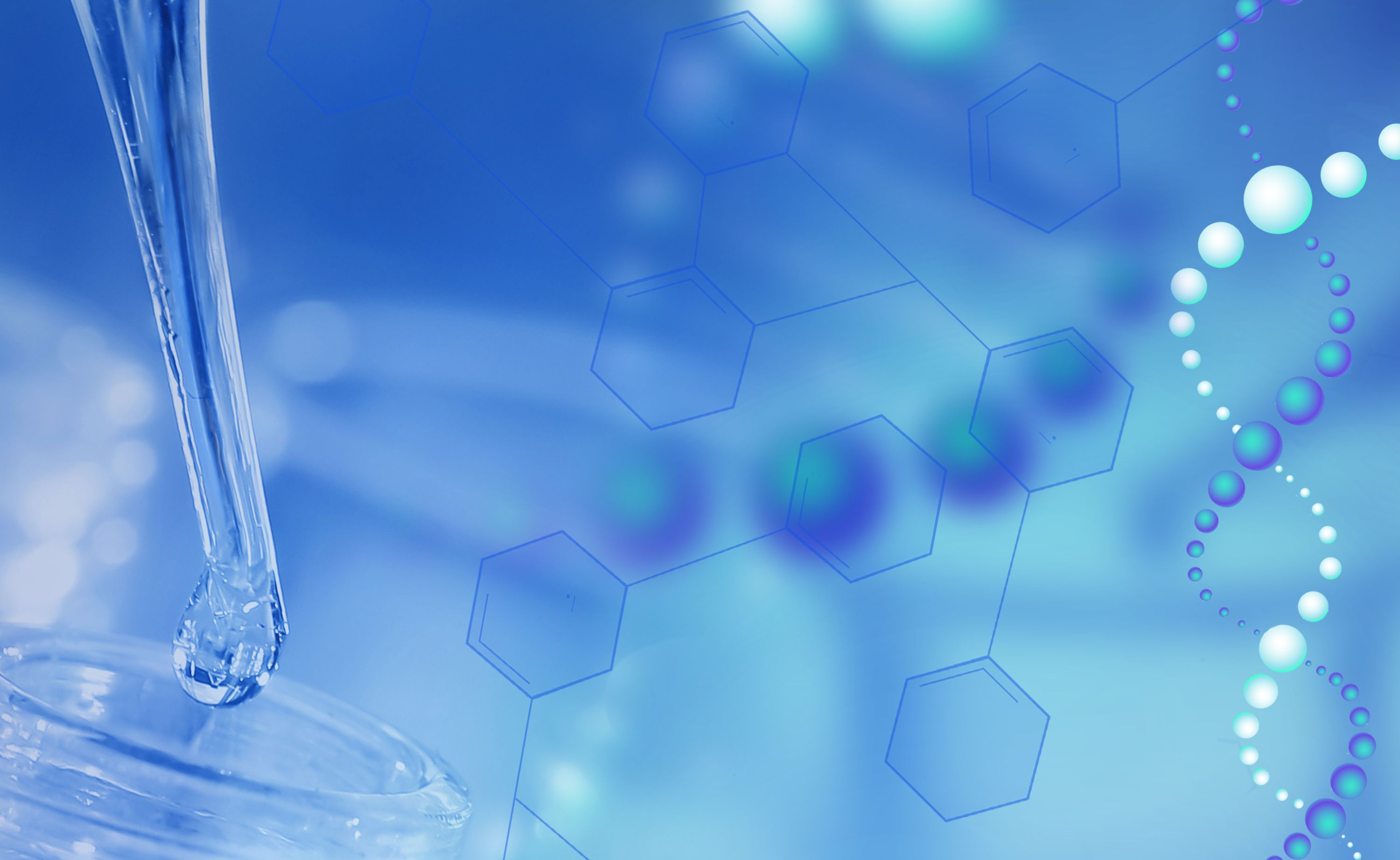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三藩之乱”肇始于“云南王”吴三桂。在8年的平藩战争中,康熙越来越意识到稳定西南对维护中央集权的重要性。
对于黔省行政区划的混乱,历代封建王朝均感棘手。由于土流并存、事权分散,导致政局不稳。据魏源《圣武记》所载:疆臣虽屡有调整贵州区划之请,“枢臣动诿勘报,弥年无成画”。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帝却认为:“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于是,一场调整地方行政机构及贵州省际疆界的工程由他手里展开。
康熙的第一个手段是裁卫并县,推动事权的统一。为此,他于康熙十年(1671年)改龙里、清平、平越、普定、都匀五卫为县,“以安庄卫归并镇宁州、黄平所归并黄平州、新平所归并普安县”。接着,下令凡明朝在贵州设置的卫所,除个别保留外,概行裁除,分别纳入各府、县(州、厅)管辖。这一举措,结束了卫所与府县分治的局面。
紧接着进行的是省际疆界的调整,这项工作主要完成于康熙、雍正两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将原隶湖广的镇远、偏桥(今施秉)二卫划入贵州,属镇远府。之后,陆续从湖南省划入镇远、偏桥、五开、铜鼓、清浪、平溪六卫及天柱县;从广西省划入泗城府、西隆州在红水河以北之土地,又将安龙、荔波、册亨、平塘、罗甸皆划归贵州;还由四川划入乌撒府(威宁府)及遵义军民府,将原属贵州的永宁县划隶四川。到清末,贵州全省共辖12府、2直隶州、13厅、13州、43县及53长官司。今贵州省界由此大致固定下来,此后再未出现大的变动。
裁卫并县、调整省界,形成了以省会贵阳为中心的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中央王朝对贵州全境的控制,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事权分散的问题。明朝虽然在贵州通过建省、平播之役,将几大土司进行了改流,只保留了贵州宣慰使司。然而,终明之世,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所形容的政治期入轨范,“黔中一省,俨然进明堂”的景象并没有出现。直到清初,境内仍有宣慰司1(贵州宣慰司)、长官司76(含蛮夷长官司21)。
康熙年间,土司领地与中央政府直接行政区犬牙交错的局面依然存在,导致地方事权割裂,政令难行,严重阻碍国家统一全国行政区划的进程。一些地方改土归流几十年后,仍为土目所盘踞,甚至“文武长寓省城,膏腴数百里无人敢垦”。而省境黔南、黔东南一带,还有大片地区“昔曾羁縻设官”,后因交通梗阻,鲜与外界交流,未曾纳入行政建制,被视为“生界苗疆”。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了当地少数民族自身的社会进步,也令清王朝的治黔政策难以推行。
在清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斗争中,土司制度已到非革除不可的地步。因此,改土归流成了雍、乾两朝治黔的重点。雍正即位后,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大规模改土归流建议。鄂尔泰认为:“若不铲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饬,皆治标而非治本”;主张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随后,大规模改土归流迅即展开。从雍正四年(1726年),清军镇压长寨地区的少数民族起,清政府相继在贵州裁废或革除了一批土司。通过一场充满血腥、急风暴雨式的改土归流,清王朝在土司地区的直接统治得以逐步建立,昔日土司专横跋扈的局面受到很大扼制。
今台江
设置“苗疆”六厅是与改土归流同步展开的一项工作。清代的“苗疆”一般指今贵州剑河、台江、雷山、丹寨、榕江及三都等地区。清政府在解决了长寨、广顺、定番(今惠水)、镇宁等地的问题以后,接着把目标转向这一带。雍正六年(1728年)至雍正十年(1732年),清军以武力攻占八寨、丹江、古州、都江、清江、台拱等地,以血与火为代价,设置起直接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六厅,即今天的丹寨(当时称八寨)、雷山(时称丹江)、三都(时称都江)、榕江(时称古州)、剑河(时称清江)、台江(时称台拱)6县。通过这一举措,昔日的“生界”纳入了清王朝的直接统治,对加强中央王朝与这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维护封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有着积极意义,也给当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但在这一过程中,清军大量屠杀少数民族群众,焚毁民族村寨,这对当地人民来说则是一场特大的历史灾难。
继稳定政局、统一行政区划之后,清政府着力推行以“抚绥”、宽缓为主旨,轻徭薄赋,鼓励发展生产的治黔方略。这些治黔方略,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历代休养生息政策再加以发展的产物。这说明清王朝虽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取得统治地位,却十分重视延续数千年的汉文化,重视吸取历朝历代休养生息的施政经验。
经过明末以来的战乱,贵州的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人民生活几乎陷于绝境。清初统治者认为,贵州一地“汉少苗多”,“昔年为贼窃据,民遭苦果,今虽获有宁宇,更宜培养以厚民生”,故“育民之道,无如宽赋”。从顺治年间开始,黔省的确屡有减免钱粮之举。顺治十七年(1660年)免贵阳、安顺、 都匀、石阡、镇远、铜仁等府属州县、卫所、土司前一年旱灾额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免当年贵州全省未完钱粮及全省前一年所有应征地丁各项钱粮;雍正七年(1729年)免全省次年额征地丁银两;雍正八年(1730年)免贵州新垦起科暨邻省改隶田亩全年额征银33300两;乾隆元年(1736年)免全省前一年所有应征银两米石,乾隆二年(1737年)免安顺等五府厅(州、县)部分钱粮,乾隆三年(1738年)免郎岱等受灾四州(厅、县)额赋并缓征旧欠,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免全省戊戌年钱粮,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铜仁府前一年应征钱粮等。
清初治黔,特别强调“宽缓”,严戒官吏邀功生事,同时也要求土司人民慎遵训诫。尤其到了乾隆时期,随着大规模战事的平息,反复强调“抚绥安戢”,加强整顿吏治,抚恤善后,恢复发展生产。在通过减轻边地民众负担、稳定政局方面,乾隆特别重视对官吏的选用。他曾在谕旨中告诫:“边疆之地,民夷杂处,抚绥化导,职位尤重,不得不慎选其人,以膺牧民之寄。”针对一些地方官吏邀功生事,他还特别严饬:“近时督、府于苗疆重地,多择能员以资弹压,殊不知矜才喜事之辈,饰文貌以欺耳目,图声誉以求升迁,非有实心实政以求抚绥化导之本,究于苗疆无所裨补……果得廉静朴实之有司视同赤子,勤加抚恤,使之各长其妻孥,安其田里,俯仰优游,一无扰累,谅无有不可以革面革心者”。
清初的捐税为田赋外之主要收入,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但清政府在贵州征税则较审慎,其取法也略有别于内地。如对贵阳等属所产之茶叶、烟、黑香、木耳、花椒、藤蔑等物,因其数量不多,免于征税。雍正时,以遵义、绥阳、桐梓等地的山场货物已在遵义、仁怀两大税处完税,下令凡分贩小场之物,官吏不得“又复抽取,重迭征敛”,并严禁“催头衙役,借端需索,侵食中饱”。至于徭役一项,则强调“地方官应恤其劳苦,加以体察,毋令兵役恣意凌虐,以肇衅端”。同时,严禁兵役到各村寨“需索酒食、盘费、鞭扑苗人及棍徒冒充差役行凶索诈,借端派累”。
清初在全国颁布垦荒令,意在增加田赋收入,扩大税源,但对贵州则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早在顺、康年间,清廷便以“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该州县给予印照,永为己业”。同时,鉴于“黔省以新造之地,哀鸿初集,田多荒废,粮无由办”,决定改为“不立年限,尽民力次第垦荒,酌量起科”。根据贵州山地情况,清朝地方官也比较重视在贵州兴修水利,认为“水利一兴,民田尽灌,商贾皆通。百姓自然殷富”。为此提出:如果不能修渠筑堰或渠堰已经废弃的,应鼓励各业主通力合作修建或恢复,按灌田多少分别给予奖励;若工程规模过大,准借司库银修筑;同时提议由官府借给工本款,仿江汉一带造龙骨车,以备灌田之用。此外,清廷还在贵州劝民饲蚕纺绩、种棉织布、栽植树木,以促进经济发展。
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辛努力,清代前期贵州的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有了较大发展,商业贸易也因之逐渐兴旺。安顺成为全省棉纺织品贸易中心,城内设有市场五个,其中三市经营棉花、一市经营土布、一市经营粮食。遵义是全省丝织品贸易中心,“秦晋之商,闽粤之贾”往来不绝。商业发展又带来了城镇和集市的繁荣。省城贵阳成为全省名副其实的经济文化中心,“江、文、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籴贱贩贵,相因坌集”。
清代前期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的重要时期,从这一大的背景来认识清初的治黔政策,其主要方面显然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而这些政策也的确产生了稳定西南边疆,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
这正是我们需要关注清代前期治黔方略的原因之所在。
(撰稿:范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