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走西口,须先从长城说起,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时期即开始修筑用于军事防御的长城,到秦始皇时期,所修长城“延袤万余里”,号称万里长城;以后汉朝、北魏、北齐、隋朝及辽、金各个时期,或对原有的“万里长城”维修加固,或根据各自的军事需要修筑新的长城。明朝所筑长城东到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全长14600多华里。明长城又分“外长城”和“内长城”,其“外长城”在冀、晋、内蒙古境内经张家口向西,又经山西大同,进入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又西行在清水河境内与内长城连接;由此继续西行经山西省偏关,进入与陕北交界的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南部。长城上设有许多关口,一般长城以南称“口里”,长城以北称“口外”,亦称塞外。16世纪中叶,阿拉坦汗统治河套时期与明朝通关互市,就是通过这些“口”进行的。
明长城在冀、晋、内蒙古地段有两个属于交通要冲的关口,一个是河北省境内的张家口,称“东口”,一个是山西省右玉县境内的杀虎口,称“西口”。但在晋陕人走西口的历史过程中,被称作“西口”的又不只杀虎口,而是张家口以西,穿越晋北、晋西北、内蒙古中部及西南部蒙陕交界地的明长城上的各个关口都被称作“西口”。一般人们从长城南边到了长城北边就叫从“口里”到了“口外”;从“口里”经“西口”到了“口外”的,就被称作走西口。有专家考证,走西口一说最早起源于山西省,因为对山西省而言,张家口在东,被指为“东口”;而他们要越过长城到内蒙古草地谋生、发展,自然要走“西口”。也是因为自清朝即流传在今山西省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的二人台剧目《走西口》,其唱词“咸丰整五年,山西遭年限……”“家住在太原,我的爹爹名叫孙朋安……”等等,致使一些人以为走西口只是山西人的事。其实不然,“走西口”有其广泛的含义,即中国历史上以山西人为多的晋、陕及冀鲁豫等省的人,越过长城到塞外,即今内蒙古西部地域务农、做工或经商,谋生或寻求发展,统称为走西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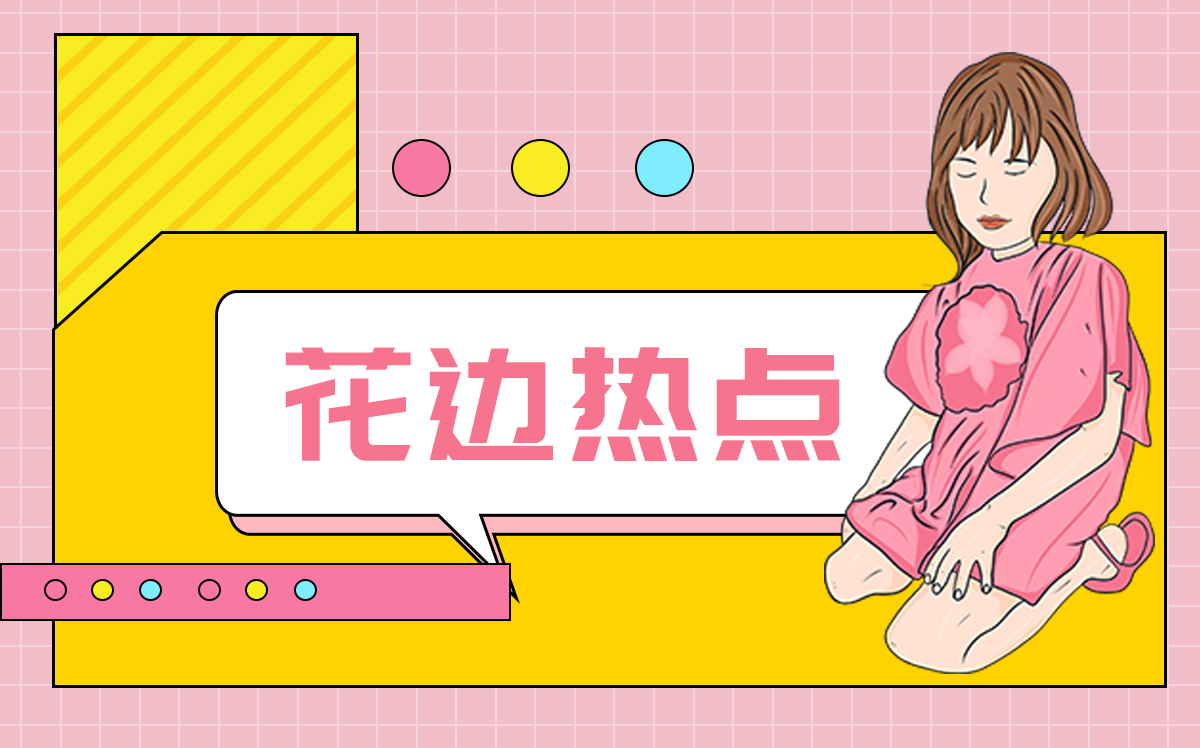 (资料图)
(资料图)
当然,当年晋、陕、冀等省的人走西口,他们各有各的“口”,都是选择邻近的“口”往外走。一般地说,晋中及雁北各州、县的人走西口多从杀虎口出关,奔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及土默川一带;晋西北偏关人则从邻近的贾堡口、红门口、关河口出关;河曲人从水西门北口、河湾渡口出关;保德人从沙河口(今东关渡口)出关。这3个县的人出关后多奔包头一带落脚或直奔后套;陕北榆林、神木人则从鄂尔多斯境内过长城关口,或在鄂尔多斯落脚,或辗转到包头、后套;府谷地处晋、陕交界,其人走西口或直奔鄂尔多斯,或走河曲、保德人走的路线到达蒙地。不管他们从哪个“口”出关,只要来到内蒙古西部草地,即称走西口。
陕北府谷县北端邻近鄂尔多斯有个重镇叫古城,晋西北和陕北许多地方的人走西口都要从这里过长城,然后通过古城关帝庙的门洞到达口外鄂尔多斯地域,所以通过古城也是许多晋西北与陕北人走西口的重要标志。有民谣唱到:“一过古城泪汪汪,一翻坝渠更心伤。”又有二人台《走西口》唱:“第一天住古城,路走七十整,虽说路不远,跨了三个省。”
至于冀鲁豫等地人走西口,路程更远些,张家口是必经之“口”,须先出“东口”再走“西口”,出了张家口,就算到了口外,对他们来说,再往前走到了归绥或到了包头就算到了“西口”了。所以历史上冀鲁豫之人,包括许多晋陕之人,亦将归绥和包头视为“西口”。
整个走西口的历史过程中,归绥和包头两个塞外重镇都起到了“集散地”和“中转站”的作用,走西口人通过这两个重镇陆续向后套、土默川、后山及整个乌兰察布地区扩散,这两个重镇也凭借晋陕冀等省人的走西口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什么时候兴起了走西口?
一般地讲,中国历史上的“走西口”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其实还要更早些,晋陕冀边民到塞外谋生,从阿拉坦汗统治河套地区时即开始了。
元朝灭亡之后,以元惠宗(顺帝)妥懽帖睦尔为首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今多伦县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国北方长期对峙,蒙古各部之间亦纷争不断。历经170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拉坦汗(俺答)占据了河套地区。
阿拉坦汗是一位贤达开明的有作为的统治者,为发展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积极主张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实现通货互市,并多次派使者与明朝谈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绝阿拉坦汗的诚意,并杀害使者,最后导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见,率蒙古铁骑旋风般穿越草原,包围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协,于隆庆五年(公元1751年),与阿拉坦汗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实现了北元与明朝间的通货互市。
此时正值明朝中叶后期,由于朝政腐败,晋陕冀边民生活十分困苦,明朝与阿拉坦汗通货互市后,无异给晋陕冀边民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便有许多穷苦边民以及因参与反对朝廷而遭官府缉捕者,为逃生或避难,纷纷越过长城,到“口外”广阔的蒙古草地上谋求生存。阿拉坦汗出于为我所用、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给他们提供土地和毡帐、耕畜和牛羊,让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或铁匠、木匠、毛匠等手工业劳动。由此揭开了晋陕冀边民“走西口”的序幕,也实现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河套地区有机融合的一次飞跃。
清入关之后,欲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隔绝长城内外蒙汉人民的联系。这是因为与内蒙古草地相邻的陕北一带土地贫瘠,连年荒旱,不仅处在极度困苦中的农民常常扯旗造反,这里还活动着一支具有强烈反清复明情绪的“绿营军”;而对曾为阿拉坦汗统领的蒙古各部,清朝更是存有戒心,唯恐长城以南带有反清思想的汉民渗入长城以北,同蒙古部落中的反清势力汇合起来,给清朝的统治制造更大的麻烦。因而清廷要对塞北河套地区采取“封禁”,限制晋陕冀边区汉民流入;但他们同时考虑到,要绝对“封禁”也是不可能的,于是顺治皇帝下旨,规定了几个“不准”,即晋陕冀边民到蒙地垦荒种地者,必须春出秋回,不准携家带口,不准在蒙地修房盖屋,不准娶蒙古女子为妻,不准学说蒙语,不准在蒙地滋事……由于这几个“不准”,就出现了晋陕冀边民来河套地区垦荒种地春出秋归的“雁行”者,在河套农业发展史写下了“雁行农业”的一页。
清朝为了实施“封禁”,还在鄂尔多斯南边沿长城北侧划了一条南北宽五十华里、东西延伸两千多华里的禁地,称“黑界地”,相当于一条无形的“长城”,既不允许陕北、甘肃等地的汉人从这里通过,更不允许北边的蒙古人逾越,同时,清廷颁布的《理藩部则例》中,对敢于私自招募汉人垦荒种地的蒙古族上层及平民以及私自到蒙古草地开荒种地的汉人,都规定了详细而繁琐的“处罚条例”。
其实,对清廷的种种禁令,并非人人都能“遵旨”,其刑律亦不可能威慑万民。内地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显突出,加之连年灾荒,致使许多晋、陕、冀等省边民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了活命,就不怕违抗皇命铤而走险;加之“黑界地”东西2000余里,清朝不可能严守无隙,违令越“界”者不可避免。所以在长城以北的河套地区也就出现了“禁者自禁、耕者自耕”的局面;清廷执行“封禁”政策也是时紧时松。
到康熙年间,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基本得到巩固,对蒙地的封锁和控制也随之放松,康熙皇帝也有意对原来的“封禁”政策做了调整,他曾说,“伊等皆朕黎庶,既到口外种田生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于是在灾荒之年放开关口,允许百姓到口外谋生,以“借地养民”。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伊克昭盟盟长松若布奏请皇上,表示“愿与汉人合伙种地,以求两有裨益”。经康熙“恩准”,理藩院奉旨下书,准许陕北汉民进入长城以北50里内的“黑界地”耕种,一时陕北汉民如潮水般涌来,50里宽的“黑界地”已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和愿望,时间一长,有人便不顾朝廷的限制,偷越“黑界地”,进入更广阔的鄂尔多斯或再往前渡过黄河到后套或土默川及后山一带垦荒种地。《调查河套报告书》记载:自康熙末年,晋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地耕种,而甘肃边民亦逐渐开殖,于是,伊盟七旗境内(包括后套),凡近黄河长城处均有汉人足迹。与此同时,晋西北、雁北和晋中地区的农民和部分商人,也纷纷走西口越过长城,到内蒙古西部或中部地区谋求生存与发展。由此康熙到乾隆年间,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晋陕汉人走西口的第一个高潮。此过程中,实际上许多原来的“雁行”者已在塞外蒙地定居下来。
应该说清朝出现过3次晋陕人走西口的高潮,第二个走西口高潮发生在咸丰年间,即如二人台《走西口》所唱:“咸丰正五年,山西遭年限……”这一时期,晋中和雁北走西口者大多经杀虎口过长城,到归绥(呼和浩特)、包头及土默川、后山(大青山以北地区)落脚,而晋西北保德、河曲、偏关及陕北府谷、神木、榆林的走西口者大多到鄂尔多斯及以北的后套或包头及周边地区谋生。
清朝出现的第三次走西口高潮在光绪年间。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清廷废除了禁止妇女出关的法令,便有更多的晋陕冀农民或商人或手工业者携妻将雏到口外定居,或年轻男子先来口外找好落脚之处再回口里接家眷或娶老婆,再来口外安家。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急于筹集巨额赔款,于1902年1月批准了山西巡抚岑春煊的奏议,对塞外蒙地实施放垦,取消内地与口外往来的各种限制,可谓“全面开放”,并派兵部左侍郎贻谷来绥远(内蒙古西部)督办垦务。这一时期,除晋陕人外,又有不少冀鲁豫等省农民走西口流入河套地区。
以后直到民国年间,晋陕及冀鲁豫人走西口持续不断。
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
爬山歌唱到:“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这无疑是当年走西口人们的哀怨心声。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离开家乡热土,泪别父母妻儿,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艰辛的日子,难免心中充满悲伤;更有留在家乡的父母妻儿,尤其是年轻的妻子,揪心扯肝,思念在外的亲人。于是他们就用唱曲儿来倾诉心中的哀怨。他们要走西口,心里又怨恨这走西口给他们带来了生离死别。那么这走西口究竟是什么人兴起的呢?
回顾走西口的漫长历史,还是走西口的人们自个儿兴起的,并不是什么人倡导、号召的,也不是官府强迫的;要说逼迫,那是人们受到了天灾人祸的威逼,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求生路,于是就兴起了走西口。
晋西北和陕北地区,自古土地贫瘠,十年九旱,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被逼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到外面寻求生路。可是生路在哪里呢?他们所居之地背靠或临近长城。自从明朝嘉靖皇帝与阿拉坦汗达成《隆庆和议》,实现了长城内外蒙汉间的“通货互市”,晋西北和陕北人与长城外的蒙古人有了联系,并从长城外面广阔的土地上看到了求生的希望。于是就有人开始了走西口,也就留下了后来一带又一代人的走西口。有民谣说:“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这个“口外”就是西口外面的世界。
最早走西口的人可称走西口的先行拓荒者,他们走进口外天地宽,虽然遭了许多罪,受了许多苦,但也开阔了眼界,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最重要的是通过卖苦力或耍手艺挣到了钱粮,秋后回到家,有人就不无夸张地向家人和邻里讲述口外见闻,草地上的人怎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河套地方怎样宽阔平坦,土地怎样肥沃,草地上怎样的马、牛、羊、骆驼成群……再看带回的银元和粮食,就不免让听的人心动,也就更相信“树挪死,人挪活”这句老话的道理,“狗儿的。明年咱也走!”这样互相“拉引”或投亲靠友,走西口的人就越来越多,如二人台《走西口》中的太春,就是因为“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才决意离开新婚妻子走西口的。
最早走西口的人中,还有因反清或惹下什么祸端而遭官府缉捕,或为了躲避兵役,被迫铤而走险,逃到口外寻求生路的。
清朝光绪年间对塞外蒙地解禁放垦之后,有的本来属于居住于晋陕边地的殷实人家,或因对当地自然条件的不满,或因邻里间发生了什么纠纷,想改变一下生活环境,便也决定走西口。他们和当初走西口的穷苦人不同的是,一般都有明显的投奔目标,带着能够带走的贵重家产如粮食、用品等,雇船渡过黄河,再雇牛车拉上东西,一路奔向落脚之地。
据史料记载,在清朝走西口的高潮阶段,山西保德、河曲和偏关各县,每年走西口者达3000~4000人,遇大灾之年,则达万人之多。陕北府谷、神木、榆林等县情况大体相同。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最早踏上西口路的是农民,走西口的主流也是农民,而走西口的农民中,人数最多的是晋西北和陕北的农民。
最早走西口的晋陕农民,或逃荒或逃难,原本都没有明确的目标,多是“旋走旋看”,如山曲儿所唱:“无根的沙蓬随风的草,哪儿掛住哪儿好。”一般地说,在哪里落脚,和每个人的自身素质、经营特长有关,有的人是为做买卖挣钱而走西口的,就大多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归绥(呼和浩特)、包头或周边的城镇落脚;有的手艺人根据自己的实力,或在城里或走乡串村耍手艺;更多的穷苦人不会做买卖也没手艺,就只好四处“刮野鬼”卖苦力,或在梁外及土默川种地,或去后套挖大渠,去后山收麦子,去后草地给蒙古人放羊;还有的去煤窑背炭,去黄河上拉船,去后营拉骆驼,去鄂尔多斯荒原掏根子(挖甘草)……一般地说,同一籍贯的人从事同一行当的人较多,比如晋西北偏关人跑河路拉船的多,保德人掏根子的多,总的来说晋西北和陕北人到口外从事农业生产的较多,而晋中与晋北“三州十六县”(忻州、代州、朔州、祁县、太谷、定襄、五台、原平、静乐、繁峙等)地方的人经商耍手艺的较多。
说到经商,就不能不说说走西口队伍中的另一支“劲旅”——商人。这些商人初走西口时都是些小商小贩,后来通过苦心经营,有的发达起来,如大盛魁的创始人,原来就是清朝康熙年间从山西太谷和祁县出来的3个随军贸易的小商贩,靠给清军供应生活用品赚钱,最先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大盛魁”,咸丰年间将“大盛魁”总号设在了归化城(呼和浩特旧城),曾发展为盛极一时的旅蒙商。还有山西祁县人乔贵发于清朝乾隆年间在包头创办的“复盛公”商号,在包头商业史及城市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更多的则是一般的小商小贩,或在城镇开个铺子,或赶个车挑个担子走村串户,卖些百姓日用商品,再换取点农副产品,来回倒腾着赚钱。
走西口对于一些大的商家来说,无疑是一条发达之路,对小商小贩来说,也不失为一条维持生计并谋求发展的希望之路;而对更多的靠卖苦力求生的穷汉而言,则只是一条求生之路,又是一条苦难之路。有一首河曲民歌便是他们所历苦难的真实写照:
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一路上数不尽艰难种种。
小河川耍一水拨断儿根,翻坝渠刮怪风两眼难睁。
此一去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回头看扔妻子撇父母实实惨心。
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住沙滩睡冷地脱鞋当枕。
铺枳椇盖星星难耐无明,上杭盖掏根子自打墓坑。
下黄河拉大船驼背弯身,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囚墩。
上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走后营拉骆驼自比充军。
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
遇灾疫遭瘟病九死一生,沙蒿塔碰土匪几乎送命。
相比之下,晋中“三州十六县”做买卖、耍手艺之人境况要好些,有人就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河曲府谷人,球也挛(干)不成,赶个牛牛车,口外做营生,还得靠个车川人。”这也许是“河曲府谷人”的自嘲,也许是那些境况较好的人对“河曲府谷人”的并无恶意的讥笑。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河曲府谷人”,并不是光指河曲和府谷两县之人,而是泛指晋西北包括河曲、保德、偏关等县和陕北府谷、神木、榆林等县之人。也许就是这句顺口溜激励了晋西北和陕北走西口之人,让他们赶着牛牛车从鄂尔多斯和土默川继续前行,到了后套或其它地域,以含而不露的潜能和不懈的努力,在那里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原标题:魅力草原——话说走西口









































